《大学》的升格运动:从“五经”系统到“四书”系统
郭晓东
“四书”、“五经”其实是一组不对等的概念,四书归四书,五经归五经。在先秦时期,儒家的经典有六种,叫“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乐经》亡佚了,到了汉代就只剩五部经典,汉代汉武帝的时候立五经博士,官方正式确认了五经的经典地位,设立了五种经典相应的博士官。
“四书”则是南宋的朱熹把《论语》、《孟子》,还有《礼记》里的《大学》和《中庸》合编在一起,并为之作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从此才有了“四书”这个说法和名称。可见“四书”的提法要比“五经”的提法晚了一千多年。同时儒家经典中还有所谓的“十三经”,这是对“五经”的扩充,其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直到南宋,随着《孟子》由子书上升为经,才有了今天的“十三经”。在中国古代学术系统里,如果某一部著作是属于经部,那么它具有最高的地位;如果不是属于经部,那么它的地位就要降一级。
中国古代的礼文化
《大学》是“四书”中的一篇,但同时又是“十三经”中《礼记》中的一篇,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礼”文化进行专门讨论。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里,“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里,“礼”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的范围涵盖非常之广。当然,它最早可能算是一种宗教行为,但是很快它就超越了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的意义,成为制度和文化的源头。比如说我们讲的国家制度、社会风俗、道德规范,当然也包括宗教仪式,都属于礼的范畴,所以“礼”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甚至可以说后来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都是跟中国礼文化有关系。唐代的孔颖达对此有个非常经典的界定,他认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古人说中国之所以叫华夏,是因为有礼仪、有章服。所谓的“章服”,“服”是指衣服,“章”是指典章。我们有“礼”文化,所以才称“华夏”、称“中国”。其实在春秋的时候,中国的版图上有很多国家,但是有的国家被认为是属于中国的,有的国家被认为是属于夷狄的,区别的标准是什么?区别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礼仪。南方的这些国家,如楚国,如吴、越等国,最早都被认为属于夷狄,但后来他们能够接受中国的这套礼仪,所以《春秋》把他们升格为诸夏。所以礼仪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三礼”与《大学》的升格
中国古代的礼文化,其基本的典籍有“三礼”,即《仪礼》、《周礼》和《礼记》。而《大学》是《礼记》的一篇。然而汉代作为“五经”中的《礼》,指的是《仪礼》,并非是《礼记》。《仪礼》据说是一部非常古老的礼仪的总汇,传统讲法认为是周公治礼作乐所遗留下来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但是《仪礼》的经文非常古奥,即便是古人也很难读得懂。《周礼》也是一部很奇怪的书,书名叫《周礼》,内容则记载了三百多种职官及其职能,相当于一部国家的宪法,是一部古人对理想政府的设计书。“三礼”中的《礼记》,其实严格来讲不是一部一个人写出的著作,它是一部杂纂之书。汉代官方的经典是《仪礼》,有很多人学习《仪礼》,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种种学习的参考资料和学习笔记等等,这些学习笔记和参考资料的汇编就成为了所谓的《礼记》。而且在汉代有多个版本的《礼记》,现存的有《小戴礼记》和《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是汉人戴圣所编,后来经过郑玄的注释,后世传习的人最多,我们一般简称的《礼记》就是指这个《小戴礼记》,而我们所讲的《大学》就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
《小戴礼记》在汉代只不过是“传”或者是“记”,只是学习“经”的辅助材料,没有上升到和“经”一样的地位。一直到唐代才被官方认为是“经”。之所以《小戴礼记》在唐代被认为是“经”,是因为所谓的汉代的《礼经》(即《仪礼》)太难读,而《礼记》里的文章好读,另一方面也由于《礼记》本身的价值,所以它的地位就越来越高,被唐人上升为五经之一的礼经。
尽管如此,《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从汉代到唐代,其实还是没有受到重视。我们如果判断古代著作是不是受到人们的重视的话,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我们看这本书被多少人注释过。而《大学》这篇文章在唐以前只有郑玄在注《礼记》的时候给它注释过,后来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给郑玄注作疏的时候再注释了一遍,也就是在汉唐之间,只有郑玄和孔颖达做过注释,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大学》这篇东西在汉唐以来没受多大重视。
意识到《大学》重要的是唐代中期的韩愈,但他仅仅是提到了这个问题而已。真正意识到《大学》的重要性,并极力对《大学》进行表彰的是宋代人,宋代关于《大学》的注释更是数不胜数,许许多多知名儒者都对《大学》有所诠释。到南宋时期的朱熹,把《大学》和《论语》、《孟子》、《中庸》合并在一起以后,就基本意味着《大学》作为新经典的地位被正式确立。所以我们说,《大学》从唐到宋升格为经典,也就是从《礼记》里面的一篇,变成了四书中的《大学》。
《大学》的升格与理学的兴起
为什么在唐宋之际《大学》会产生这么一次升格运动?其实伴随着《大学》以及另外一部书《中庸》的升格,中国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型,也就是从原来的汉唐经学形态转到了宋明理学。首先我们来看宋明理学为什么会兴起?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一个是当时宋代的儒家认为汉唐儒学没落了,丧失了应有的生命力。另一个是宋代的儒家认为佛教在中国太猖狂了,儒教要捍卫自身文化和价值取向。所以宋明理学的兴起有这么两个历史背景,而《大学》的升格恰逢其时。
儒家的经学在汉代达到了一个顶峰。汉代的经学讲究的是通经致用,经学是为现实服务的,但是另一方面汉代的经学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病,就是汉人对经典的注释越来越烦琐,有时候一两个字要注释个成千上万言,烦琐且没有意义和价值。唐代虽然在政治上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但是在儒家学术上的建树是很小的。唐人只是把传统的经学进行了汇编,并且做了一个标准教科书式的解释,但是标准教科书式的解释导致了儒家经学的最后一点生命力也消失殆尽了,正是因为如此,宋以后的儒家对唐代的儒学非常的不满。
与此同时,随着儒家自身的式微,则是佛、老两教的兴起。佛教在汉代末期传入中国,经过魏晋时期的消化和吸收,到了唐代达到了一个顶峰,真正实现了中国佛教的转变和完善。在唐代影响最大的是禅宗,其中六祖慧能讲究明心见性,不读书也可以直接明心见性。这个理论对传统的士大夫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当时第一流的人物都被佛教吸收过去了。因为儒家不能够提供安身立命之本,而佛教能够,因此在当时的士人看来,儒家如果要复兴的话,首要的使命就是要从这些和尚手里夺回儒家本来拥有的精神统治权。而禅宗之所以对读书人有这么深的吸引力,不外乎就是他们那一套明心见性的理论,有一套心性之学。而儒家要重振他们的生命力,也应该开出儒家自身的心性之学。
其实早在唐代韩愈那里就试图从传统的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精神资源,他已经发现了《大学》的重要性,他看到了《大学》里面讲的正心诚意等等理论,他指出了在儒家的经典中也有修心法门。而且《大学》既讲诚意正心,同时还讲修齐治平,这一点就跟佛教有着很大的差异。佛教要“舍离世间、灭弃天常”,要修炼身心的话,就一定要出家。《大学》则一方面可以讲诚意正心,另一方面还讲修齐治平,这样,我可以不离世间来修炼我的身心。这要比佛学高明。
韩愈之后,宋代的儒者就努力地从先秦的儒家经典中去寻找一批这样的资料,他们发现了《大学》,还发现了《易传》、《中庸》和《孟子》。从北宋胡瑗、司马光等人开始,就对《大学》、《中庸》进行了注释。理学的开山祖师二程兄弟都非常重视《大学》,他们认为《大学》是学者入门的教科书,也就是说,你入我门来,先学《大学》,学完《大学》之后再学别的。后来二程兄弟的三传弟子朱熹就正式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编在一起,写了一本《四书章句集注》,从此才有了“四书”之名。而到了元代,官方的科举考试又正式地把朱熹的“四书”作为官方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从此,“四书”就成为了天下读书人所必读的书。
以上讲了一个简要的思想史的历程,下面我们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即作为“四书”系统的《大学》,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大学》与道统
首先,从“五经”系统到“四书”系统的变化过程中,作为四书系统的《大学》,被认为是儒家道统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谓的儒家道统传承,指的是儒家的一个传道谱系。本来儒家是无所谓传道谱系的,但是我们知道,唐宋以后的儒家要应对的是佛教的挑战,而在佛教,则有一个历代祖师相传的传承谱系。于是儒家为了论证自己历史与文化在当下的合法性,就必须也有一套自己的传道谱系。这样遂有了韩愈的道统说。在韩愈看来,儒家的道统体系是从尧、舜、禹开始的,接着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但是儒家的谱系到孟子以后就结束了,所以韩愈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轲之死,不得其传也”。在韩愈看来,秦汉到唐的这一段时间里,儒家的道统就没能传得下来,也就是说,在汉唐以来,虽然有儒学,但是这些儒生所传的不再是儒家的道,仅仅是学而已。
后来宋儒基本上承认了韩愈所讲的这么一套儒家的传承体系,也就是儒家的道统,也承认了韩愈所说的“轲之死,不得其传也”,但是他们做了略微的修正,在孔子和孟子之间进行了补充。在宋儒看来,既然已经发现了《大学》和《中庸》这两本书,那这样就正好在孔孟之间补充上了一个应该有的传承环节,于是就认为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传道给子思,再由子思传道给孟子。宋儒认为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所传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大学》;后来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也留下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中庸》,子思又传给了孟子。于是后来朱子所编撰的“四书”相对应的就是孔子、曾子、子思和孟子。
就曾子和《大学》来说,朱熹认为,《大学》是由孔子和曾子两个人共同完成的。《大学》文本的形式比较特殊,前面第一段是一个总论,然后从第二段开始对总论的每一句话都做了细化的分论。所以朱熹说第一段的总论是《大学》的经,是孔子亲自作的;后面分论的部分,他称为是《大学》的传,则是曾子所作。所以传统上就说,《大学》是由曾子所作。曾子所传的就成为了宋以后儒家的正统,所以曾子在宋以后的圣人谱系里被称为宗圣,子思被称为述圣,然后孟子是亚圣。宋以后对儒家圣人谱系的建构,就是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相应地,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为了宋以后儒家最基本的著作,也就是“四书”。
不过,即便是从宋明以来,对于《大学》到底是不是曾子所作,也有人一直存有疑问。民国以来,很多学者举出了非常多的例子来论证《大学》这篇文献不可能是孔子到曾子这个时代能够完成的,也就是说《大学》的成书年代最早只可能上溯到秦。因此,现代的一个非常主流的观点认为,《大学》可能是秦汉之际的某一个不知名的儒家所作,《中庸》也是这样。但是,在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批竹简,人称“郭店竹简”,这批文献是先秦时遗失的一些儒家古文献,经过许多专家的研究,认为这些文献里有传统上所讲的子思、孟子这一系的东西,文本的风格和《大学》、《中庸》相似,所以有人又开始重新怀疑,也许《大学》还真的是曾子作的,《中庸》也许真的是子思作的。但是《大学》是否是曾子作的,没有一个定论,我们只能说大概是这样。
《大学》的文本差异
其次要讲的就是文本的差异。如果我们去读《礼记》中的《大学》,我们就会发现段落之间的衔接似乎不是非常密切。所以在宋代,很多儒者认为传统的《礼记·大学》有错简,相应地在宋代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大学》改本,有的人认为这个字是错的,我要把它改过来,有的人认为这个顺序是不对的,我要把它重新换一下顺序。这样的话,在宋代的《大学》版本就有了上百种之多,但是最经典的还是朱熹的改本,后来作为科举考试用的《大学》就是用的朱熹的注本和改本。不过,通过两个版本的对读,我们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版本上的问题,里面还涉及非常深刻的义理系统的差异性。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比如《礼记》本的《大学》,第一句话叫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有人认为应该是“新民”。事实上在古书里就出现过这个“亲”跟“新”互相写错的现象,所以宋代的二程和朱熹都认为“亲民”不对,应该是“新民”,那么这里有什么特别玄奥的地方呢?如果讲作“亲民”的话,就是说人民应该是统治者所要亲爱的对象,比如说汉代的地方官往往被称为“亲民官”,他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同时还要负起一定的教化人民的使命。本来让人民有所教、有所养,这是儒家的通义,但是在汉代讲亲民的话,这个“亲”字又有特殊的考量。在汉儒看来,人民之所以要被教化,是因为人民是冥顽不化的下愚之人,汉代的儒者对“民”有这样的解释,“民者,冥也”。“冥”就是眼睛睁不开,所以人民是闭眼的、愚昧不化的下愚之人,如果我们不进行教化的话,人民永远没有办法自理。但是宋代改“亲”为“新”,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宋儒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使命感,他们要“以斯道觉斯民”。宋儒认为他们不但继承了孔孟以来的道统,而且还要用孔孟之道来觉悟我们的人民,这叫“以斯道觉斯民”。这里的关键点就是一个字眼,叫“觉”,相对汉儒来讲,宋儒认为人民是可以被觉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睁得开的。更进一步,宋儒认为人民不但是可以被觉悟的,而且是必须得觉悟的。老百姓之所以能被觉悟,宋儒的理论依据是孟子的性善论。所以“新民说”的提出,无疑是重新接续了孟子所讲的性善论的传统,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们内在的明德,所以《大学》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每个人都有内在的明德,不管身份如何,都有被教化、被觉悟的可能,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这和汉人的说法就不一样,汉人说你可以被教化成为一个良民,但是你成不了圣人,但是宋儒说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
《大学》之为“大学”
第三,我想解释一下《大学》何以是“大学”。“大学”两个字在汉代读作“太学”,宋代的朱熹把它改成现在的读法。“太学”,是汉代郑玄的读法,郑玄在注《大学》的时候,认为这个“大”字应该读“太”,所谓的太学,它的意义是“博学可以为政”,这句话是针对天子王公而言的。而宋代的朱子认为,这里的“大”应该是指“大人之学”,而和这个“大人之学”相对应的就是“小学”。朱熹在《大学章句序》里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说小孩8岁入小学,所学的是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待人接物的基本仪节。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一个人如果学了小学,则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基本行为准则就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到了15岁,年纪大了,就要学一些伦理、政治、哲学等更高深的学问,那么这就是“大学”。之所以要学那些伦理、政治、哲学等高深的学问,在朱熹看来,我们在小学阶段,虽然学会了待人接物的基本仪节,也学会了基本的行为规范,但是我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朱熹认为,按照“大学”之道,作为学生,我们不仅仅应该这样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学”和“小学”有着很大的差别,可能你学了“小学”之后,在社会普通标准来说已经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学了大学,你就可以“止于至善”。
不过,这里讲的“大人之学”的“大人”,不仅仅是指相对于未成年人的成年人。“大人”这个词,在古代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指成年人,朱子讲的15岁以后入大学,很显然是指成年人的学问。第二层的含义,这个“大人”是指执政者、贵族阶层。在古代,“大人”是指这些具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指政府的官员,这是第二层含义。第三层含义是指有德的人,“大学”之所以是“大人之学”,因为它讲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所以它理所当然是用来教育执政者的政治哲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大学》又以修身为本,所以当然也就是成就有德者的学问。
在孔子之前,所有的教育都仅仅局限于贵族阶层,而孔子则对来求学的学生一视同仁,不问身份和地位。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在孔子的弟子里面,真正具有贵族身份的人其实是很少的,除了南宫敬叔与司马牛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大多数出身贫贱。孔子通过他的教育,导致了学术下移到了平民阶层,导致了平民能够通过学习跻身于统治阶层。更重要的是,孔子所教的不仅仅是政治的技能,孔子的教育更包含德行的内容,或者说更多注重的是德性方面的内容。所以通过孔子的教育,“大人”这个词的含义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人”这个词专指贵族,专指那些有身份的人,但是通过孔子的教育,“大人”的含义慢慢地变成了道德高尚的人。同样地,“君子”这个词的含义也由“位”转变到“德位兼言”。相对地,“小人”这个词本来只是指普通的庶民,是没有道德含义在里面的,但是在孔子之后,则更多地是指那些德性卑劣的人。
那么作为儒家来讲,理想的执政者应该是德才兼备的,这一点我们在读《论语》时也看得很清楚,并且德是第一位的。当然,最好是能够德才兼备。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只是一个理想,我们也都知道,实际上理想跟现实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冲突,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未必是有德之大人。但是《大学》作为一本教科书的目的,却是希望那些准官员们能够首先成为有德之大人,进而在他们上位以后,真正成为有德有位之大人。《大学》就是为了这样一种目的而编写的教科书,所以《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修身”是前提。但是在“修齐治平”之前还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且一定要遵守这个次序,如果你没能够通过前面的“格致诚正”,后面的“修齐治平”是谈不上的。可见治国平天下并不在于你是否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而在于你心地上的功夫如何,所以朱子讲《大学》作为大人之学,他更看重的是有德者的“学”。
学习次第
“四书系统”是朱子奠定的,而且朱子认为,在“四书”内部,《大学》也有它特殊的地位。《大学》有三条基本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又有八条目,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三纲领、八条目在朱熹看来,是学习的最基本的规模,所以入门就应该由《大学》入手。因为《大学》是最基本的坯子,从这里入手,间架搭好了,之后就是填充材料了。因此朱熹虽然编辑了《四书》,但他认为《四书》之中,学习也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就是以《大学》为首。所以朱熹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只有树立了“三纲八目”这样的规模之后,然后才可以读《论语》以利其根本,之后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所谓的“发越”,是从内在的精神上说,因为《孟子》的内容比较张扬,让人读起来比较有激情。最后读《中庸》,来看古人的微妙之处,因为《中庸》讲的东西相对来说要难理解得多。《大学》是我们很容易看得懂的,一般读者不需要怎么讲解也可以自己看得明白,但是《中庸》的内容就比较微妙、比较玄妙,里面讲到的很多内容一下子都很难懂。所以朱子说读《四书》的次序应该《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大学》要先看,不仅在于它有它的规模,而且它好读。《论语》相比《大学》就有一定的难度,虽然《论语》很平实,但《论语》是散的,不像《大学》就那么一篇,而且文字结构非常紧密,都是围绕着三纲领、八条目来讲的,三纲领、八条目讲完了,这篇文章也就完了。
在朱熹看来,《四书》和《五经》亦有次第,只有《四书》读熟了你才可以去读《五经》,否则就是好高骛远。所以整个学习的次第就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和诸子。如果你行有余力,那么诸子百家都可以读,但一定要把《大学》读实了,只有在《大学》的坚实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学习。我们不妨按照朱子的次第去读书,相信一定会有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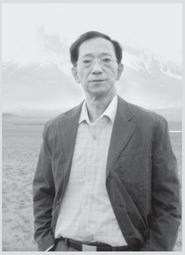
王纪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研究专业。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文艺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学风格论》、《文学:理论与阐释》、《文学的速朽与恒久》等著作。主编《中国现代散文欣赏辞典》、《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欣赏辞典》、《文艺学与语文教育》、《大学语文基础》等。《浅论怪诞》获上海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文论的三原点和元结构》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
- 先 典 新 识——名家人文与经典演讲录第一辑
- 上海青年人文经典读书工程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