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娟:明末清初三大散文家之一侯方域的散文创作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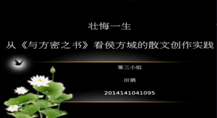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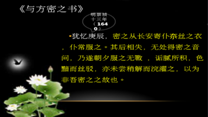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第三小组的田娟。这次我主讲的话题是明末清初三大散文家之一侯方域的散文创作实践。主要是从他晚年的一篇作品《与方密之书》来做一个文本细读和延展探讨。
侯方域。字朝宗,号雪苑,晚号壮悔。明万历四十年(1618)出生。顺治十一年(1654)冬,因病去世,享年仅三十七岁。
下面我就直接从他的作品《与方密之书》具体看一下他的散文创作。
《与方密之书》写于顺治十年,也就是侯方域去世前两年。其中体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基本上都是侯方域较为成熟的阐发。方密之就是方以智,和侯方域一样,是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是作者的好友。清兵南下广东,他辅佐桂王抗战,不久罢归,削发为僧,以这一特殊方式保持自己的晚节。作者知悉后,托人捎去此信,表示崇敬和眷念的心情。下面是我从文中选取的两段精华做一个文本细读。
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可从道。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夵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斁,诟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浣濯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后,制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熏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歔。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制,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嫣。”
这里是一段细节描写,描写对故人方密之所赠之衣的珍爱情状。十三年前,方密之送给侯方域一件蚕丝做的衣服,之后两人之间失去了联系。在这期间侯方域经常穿着这件衣服。即使“诟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浣濯之”就可以看出侯方域对这件衣服真的是真爱,衣服油腻不堪,褪色掉丝也不脱下来换洗。虽然是夸张的写法,但是,侯方域对这件衣服的珍视是显而易见的。十三年不仅是时间的流逝,更是朝代的更迭,方密之送给侯方域的衣服是明朝服装的样式,而今已是清朝的天下。方域不敢再穿,只能供奉起来日夜对其唏嘘不已。但是也不愿改制样式。要保留衣服完好如初的样子。表示我对密之的珍重。这一段细节描写,详尽细微,处处着意,感人至深。方域对密之的友情的珍视,从方域对这件衣服的珍视衬托出来。
然而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代,衣服不仅承载了方域对友情的珍重,更是由此延伸出方域对遗民节操志尚的讴赞。我们再看下一面的这一段描写。
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
这里方域运用了两个典故,分别以郑思肖和陶渊明的故事来表达对遗民气节的崇敬。郑思肖,南宋诗人、画家。宋朝灭亡后,隐居于吴中僧寺,坐卧必向南,画兰、梅不画土,表示国土已被人夺去,借以表达亡国之痛。陶元亮,就是著名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入南朝刘宋以后所作的诗,仅书甲子,不纪年号,以示思念晋朝。(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但此处方域引用之意应是这个。)最后的“共评玩之”表明自己与方密之的志趣相投,也清楚的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侯方域羡慕他们能坚持民族气节,这其中又何尝不隐喻着他对新王朝的不满和对故国旧土的怀念之情呢?回到现实,闽兰粤竹,大明江山全遭清兵铁蹄践踏,侯方域有着难以诉说的亡国之痛。更是体现着明显的壮悔之意。就在写这封信的前两年,侯方域参加了清朝的乡试。(学界对于他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存在争议),但是这件事确实对他的晚节造成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晚节不保的污点。)朋友方密之以削发为僧保持自己的晚节,历史上的诸多贤人也保持着高尚的遗民节操,方域在表示对他们的崇敬之情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郁闷,后悔。当然,从更广阔的一点来说,壮悔表达的是对自己一生仕途坎坷,无所作为的愤懑、愁苦之情。下面简单看一下侯方域这短暂的一生。
总的说来,侯方域的人生经历中,七至二十二岁,为读书游学时期;二十二至二十八岁,为主盟文社时期,二十八至三十七岁,为伏处隐居时期。侯方域短暂的一生经历了早期的年少轻狂、意气风发;中期的仕途失意、颠沛流离以及后期的愁苦愤懑、悔恨交加。而正是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影响了侯方域的散文创作的转变,从六朝骈体文到继承唐宋古文传统的转变。主要是学习唐宋八大家“文以载道”之风。体现出侯方域对唐宋古文“社会功能”的偏爱,表现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虽然侯方域一直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但是方域对现实的关注始终不减。他的作品很多都带有现实主义风格。或是斥责权贵;或是讴歌遗民的高尚情操、或是叙写小人物的传奇人生。《与方密之书》只是侯方域众多优秀作品中的一篇,其中的细节描写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刻画书写的淋漓尽致。方域文风豪迈不羁,自成一格,为清初文坛带来新的气象,也促成了清初经世致用之风的最终形成。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