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关注:重商主义就等同于贸易保护吗?——对于重商主义理论的重新解读
三、今日财经关注
重商主义就等同于贸易保护吗?——对于重商主义理论的重新解读
作者: 姜达洋 天津商业大学 来源:《现代财经》2019年第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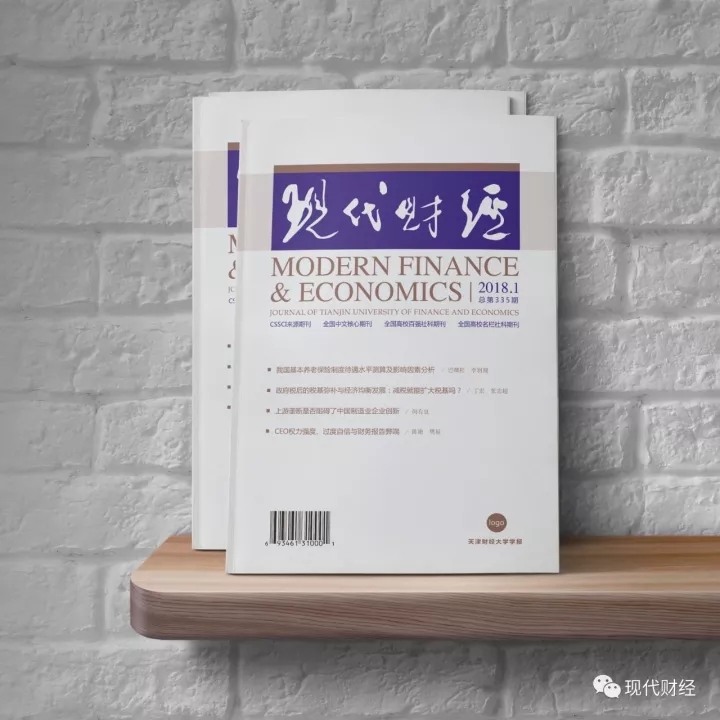
摘 要: 长期以来,重商主义经常被狭隘的与贸易保护主义等同起来。随着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经济中的复苏,甚至有一些学者把当前新保护主义盛行的全球经济思潮称为新重商主义。本文通过梳理重商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打破传统的思想框架,提出重商主义的核心为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而贸易保护仅仅是其产生初期的主导政策,而非贯穿于重商主义全过程,从而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发掘重商主义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理论体系;民族主义;国家垄断主义 论文摘引:姜达洋.重商主义就等同于贸易保护吗?——对于重商主义理论的重新解读[J/OL].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09):86-96[2019-09-12].https://doi.org/10.19559/j.cnki.12-1387.2019.09.007.
作为一门前斯密时代的松散的经济学说,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重商主义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在国内外最权威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中,对重商主义思想的解读往往也语焉不详,仅有寥寥数页。很多经济学者们往往简单地把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划等号,将贸易保护视为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甚至是唯一的政策重心。无论教材、专著,抑或最新的学术论文中,把贸易保护直接等同于重商主义的标签式的经济观点比比皆是。
在经济自由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中,被标注着封闭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重商主义思想始终保持着负面的形象。然而,从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到大萧条,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腾飞,再到今天的特朗普贸易保护思想,一贯被视为歪理邪说的重商主义却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轮回中一次次重生,尽管饱受批评,其理论的价值却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屡次闪耀。在贸易保护思潮复苏的今天,重新正确认识重商主义思想的价值,从西方经济理论的演进与现代经济史的发展视角,重新反思重商主义的价值就愈发显得重要了。本文正希望通过对于流行的对于重商主义的误解着手,全面地梳理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演进脉络,重新发掘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价值。
一、重商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即使在最为流行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中,对于重商主义,以及重商主义代表人物与思想,也缺乏清晰的界定,而更多围绕财富观,贸易观和具体的政策思想等松散的观点,而以少数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来代表其理论思想。与后世的众多经济学派相比,经济理论界对于重商主义的研究往往缺乏从理论体系的发展与演进的视角上,对其理论观点的清晰梳理,这才导致更多的重商主义学者的经济观点泯没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不为世人所周知。
在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理论框架下,学术界通常把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视为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名著《国富论》出版之前流行于西欧各国的经济政策体系,或者是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诞生之前,社会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拉尔斯·马格努松(Lars Magnusson)甚至将重商主义的思想流行时期精确地界定在1620-1776之间[1],但是实际上,重商主义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14世纪。而公认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最为盛行的时期为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中期,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末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的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当政时期,成为重商主义政策思想的全盛时期,其政策思想几乎主导了当时西欧各国的政策选择,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该政策思想广泛盛行于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在内的西欧地区,甚至这一时期的德国,以及斯堪德纳维亚地区的政策也可以看到重商主义的影子。
“重商主义”一词最早以“重商主义体系”(System Mercantile)的形式出现于米若比(Mirabeau)的《自1763年以来的哲学原理》一书。而它真正广为人知,还是得益于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其的尖锐批评。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不同时代和不同国民富裕的不同发展,就其使人民致富而言,而生了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个可以称为重商主义体系,另一个可以称为重农主义体系”[2]。在书中,斯密把重商主义界定为为追求民族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利用限制进口或补贴出口等保护性政策手段,推行的一整套系统的国家特权机制,并几乎用了《国富论》的整个第四编来批判重商主义,以及它们所代表的17、18世纪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经济学说和政策选择,也使得古典经济理论诞生之初,就把重商主义置于其对立面位置。《国富论》的出版,固然被视为现代经济理论的起源,同时也被视为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终结。
在古典经济理论占据主流地位时期,尽管在以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亨利·凯里(Carey Henry Charles)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以威勒姆·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和现代幼稚产业保护理论集大成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论体系中都可以看到诸如追求民族国家利益、贸易保护、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等明显的重商主义痕迹,但这些后世的经济理论都已经不能被简单纳入重商主义的范畴了(4)历史文献中的新重商主义,主要是指1870到1920年间,英国经济史学的兴起,及其倡导的关税改革运动,另一种观点中的新重商主义则是指一战结束至大萧条期间,胡佛旨在发展美国制造业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事实上,这两个时期都伴随着明显的关税提升,从而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直到上世纪中期,雅各布·维纳(Vilar Jacob)的《亚当·斯密之前的英国对外贸易理论》[3](1930)和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的《重商主义》[4]最终完成了对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梳理,成为当代研究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最为权威的理论成果。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以呢绒、羊毛为代表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先后萌生(5)16世纪初,呢绒和羊毛出口占到英国出口总额的79%,成为当时新兴工业的主要部门。,皇权专制在欧洲全面建立并巩固,沉重的税负和频繁的战争给各个中央集权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一大批以商人、地主、官僚、教士为代表的统治精英在各种利益力量的驱使之下,针对当时民众所关注的贸易、货币、利率、税收等主题,发表一些篇幅简短的小册子,以推广个人政治,经济思想,说服民众,更重要的是说服政府采纳自己的经济政策建议,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重商主义理论的起源(6)熊彼特把这些重商主义思想家称为“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家”。实际上,现存的主要重商主义文献都表达了相应作者群体以一种直白或者隐晦的方式追求特殊经济利益的经济、政治诉求。。
然而,尽管自亚当·斯密起,重商主义就被视为一个理论学派而存在。实际上,17、18世纪诸多重商主义学者散乱的观点更多表现为针对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而非逻辑清晰,结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熊彼特(Schum Peter)认为,由于“重商主义作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借助于常识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论点……他们并没有透过问题的表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只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才需要运用分析技术。他们提出论点后,便匆忙提出具体的建议……”,因此,他认为“大量(重商主义)的文献实上是处于分析前的阶段,不仅如此,而且是粗糙的——是非专业人员的著作,甚或是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著作,这些人往往缺乏阐明基本原理的技巧。”也正缘于此,熊彼特才将重商主义理论称为“虚构的体系”[5]。
事实上,对于重商主义并不成体系的批评并不罕见。A·V·加杰斯(A·V·Judges)批判重商主义根本就缺乏一个核心与共性的教条,因而认为“重商主义是由这样一些人创造的,他们由滥用其先辈的令人怀疑的古怪想法并将这些材料附加到他们的信念上”[6]。理查德·威尔斯(Richard Wiles)认为“将重商主义视为盛行于几个世纪的固定思想流派或内在一致的教义是一种徒劳,且无济于事……尽管重商主义可被视为一种思潮,但是否可将它总结为一种经济政策的特殊走向是值得怀疑的”[7]。威廉·巴贝尔(William J Barber)则提出正是由于“商人作者们在英国重商主义的全盛时期确实也并未形成一个同质的学说团体”[1]才导致了经济学史中对于重商主义的情绪化的指责,使得无论重商主义政策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多么流行,却始终缺乏足够的学术性的尊重(7)此处所言的重商主义就是指以汤因比、坎宁汉姆、阿施利和海文斯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史学派,也是理论界所认同的“新重商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与其说重商主义是一个逻辑清晰,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如说它是一个时间概念,仅仅是前斯密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大杂烩。可以说除魁奈(Fransois Quesnay),杜尔阁(Anne-Robert-Jacqnes-Turgot)等著名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和配第(William Petty)、洛克(John Locke)、诺思(Dudley North)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外(8)事实上,所谓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借助于攻击重商主义而扩大社会影响,而另一方面,二者的经济观点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人物配第在就业政策,价格管制的观点非常接近于当时的重商主义观点,而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达维南特一方面继承了托马斯·孟的贸易差额思想,另一方面又是配第的政治算术的忠实的追随者。值得注意的是,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熊彼特甚至把配第、诺思等著名的倡导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作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纳入到重商主义作家的行列,这显然与把重商主义等同于保护贸易的传统经济思想史观相矛盾。,17、18世纪在西欧国家通过发表小册子,公开政治经济观点的所有经济学者都被囊入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范畴。
当然,在经济思想史中,一提起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往往喜欢将其与贸易保护结合起来,因而以重金主义为标签的杰勒德·德·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以贸易差额论广为人知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因追随政治算术而誉为数量分析的鼻祖的查尔斯·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的经济思想就成为经济学教材中重商主义的代表,而这些知名重商主义者莫不高举贸易保护的经济武器,旨在维护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公司的垄断利益,这更固化了将贸易保护等同于重商主义的理论错觉。
在一些学者看来,重商主义似乎是一个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理论体,他们不但无法像其它经济学派那样拥有共同的方法论或政策主张,相反很多知名的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甚至与传统理论所认同的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相差甚远,例如传统观点认为重商主义普遍强调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特别是贸易保护政策,而为特定阶层创造出高额垄断租,实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然而,达维南特却严厉地批判了英国政府的外贸管制政策,乔赛亚·蔡尔德(Josiah Child)甚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早期重商主义赖以生存的核心的垄断特权。而且很多重商主义者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比如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与约翰·海尔斯(John Hales)对于自利能否实现公共利益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在17世纪20年代的贸易危机面前,马林斯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更是针对是否应该进行贸易管制问题,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小册子论战,但这也无损于他们同为最著名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地位。诸多重商主义学者之间的论争,更模糊了重商主义的理论框架,这才导致了自亚当·斯密以来,标签式地将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特别是最能够代表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经济政策选择的贸易保护思想视为重商主义理论核心的偏见愈演愈烈,其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反而不为人知,这种标签化、脸谱化的理论研究传统直接导致了重商主义长期被错误地置于经济学研究的对立面,其历史价值长期为世人所漠视。
也正是由于重商主义横贯了西欧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漫长历史,见证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与成长历程,特别是以政治宣言和小册子方式表达经济观点的方式更决定了其发展演进过程中,不同学者的观点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使在主流经济思想最为关注的贸易保护方面,也从德·拉斐玛(de Laffemas),托马斯·史密斯和格莱欣(Thomas Gresham)等早期重商主义学者主张的完全禁止所有制造品进口,禁止任何会使货币从王国流出并转入外国人之手的市场交易,禁止出口原材料的重金主义思想,过渡到托马斯·孟和达维南特等主张的贸易差额理论,而在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货币价值、公共目标、税收制度和产业政策等问题上,不同时期的重商主义学者的观点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分歧,这更加增加了重商主义思想研究的复杂性。
二、重商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重商主义所盛行的17、18世纪是各种类型经济观点不断涌现、论战、碰撞的年代。重商主义学者们的研究主题也极为散乱,从货币价值、国际贸易、税制、劳动与就业政策、垄断特权的设置与分配、产业管制与扶持等,包罗万象,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方面。然而,透过杂乱的研究对象,迥异的政策主张,抽象其理论的核心,可发现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贸易开放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问题(9)在笔者看来,斯密在《国富论》(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其实正是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以来,自重商主义学者而始的社会经济论战的核心问题,分工、交换、自由贸易与市场机制仅仅是斯密设想的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核心力量,而这些问题在众多重商主义作家的小册子中都得到了深入的论述,从而在重商主义理论与古典经济理论之间搭起了一道桥梁。。重商主义理论的产生与演化,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崛起时期,代表着新兴商业经济利益的商人,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谋求与处于强势统治地位的王权政治联合,固有的封建君主,新贵族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之间的折衷,乃至合谋,从而寻求在统一的国家政权下争取民族崛起的政治诉求,也成为分散化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集中化、规模化、垄断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跃进过程中的过渡性指导思想。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欧各国相继出现,新兴的商人阶层希望打破教会对于社会经济的束缚。始于14、15世纪的宗教改革,使得诸多西欧城市得以摆脱教会封建贵族的掠夺和束缚,从而在日益强化的专制王权的保护下,实现自治,进而焕发勃勃生机。以往天主教会对于民众的强烈的思想垄断被打破,政教分离推动了君权的强化,思想解放则促进了资本主义人文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广为流传,社会思潮涌动,这都成为重商主义的兴起的社会土壤。
宗教改革引发了更多的宗教压迫与宗教战争,法国亨利四世(Henri Ⅳ)遇刺引发了法国内战,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荷兰加尔文派为追求民族独立与西班牙军队之间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新教徒在英国的领导地位,一系列的宗教纷争逐渐为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战争所带来的劳动力的广泛流动进一步优化了像纺织业这样的新兴产业在欧洲的配置,在加剧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的同时,又进一步推进了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
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压力下,各国政府相继提高税收水平,力争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以应对战争需要。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西欧各国的专制王权也纷纷意识到需要联合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完善政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制的建立健全,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新兴商人阶级自然成为极权政府争取的对象。从某种意义而言,重商主义的兴衰恰恰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发展对于专制王权从依赖,联合,再到排斥的发展演进过程。
如果运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SRPS)来研究重商主义理论体系的话,在笔者看来,重商主义经济观点的硬核,或者说核心理论只能是民族国家经济建设,而主流经济理论所关注的财富观,贸易保护思想,货币理论都仅仅是为了维护这一核心思想的诸多保护带,或者是为了追求民族国家的经济建设这一最高目标,而由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仅仅是支持重商主义理论硬核的政策手段,而非与之平行的核心思想。
其实,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施穆勒也曾经提出类似的经济观点,他明确指出重商主义的“内核是国家建设,不是狭义的国家建设,而是国民建设和民族经济形成的同时进行……这一体系的本质不在于其货币理论,或贸易平衡,不在于关税壁垒,保护税,或航海法案;而在于更为宏大的事物,也就是在于社会和制度的整体转型,由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代替地方的和领地的经济政策”[8]。
熊彼特也认为,尽管传统教义上的重商主义体系的核心是贸易差额,而且贸易差额甚至被很多经济学家误以为就等同于重商主义体系,但是重商主义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出口垄断主义、外汇管制和贸易差额三个题目[5]。而之所以经济学家们把贸易差额等同于重商主义仅仅是由于斯密在《国富论》的第四编中,针对重商主义的攻击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差额这一个论点上而已,虽然斯密并没有完全忽略其余两个重要问题。正是这种误解才导致了重商主义被视为与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观点,而受到广泛的批判。
重商主义所引发的争议并不仅仅存在于理论,而更多表现在其政策的实践之中。特别是,重商主义时代的很多政策都可以追溯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因而具有不公正的利益再分配的色彩,这也成为后世很多学者对于重商主义批评的理由所在。然而,在熊彼特看来,只有站在这些利益集团的角度上,才可以真正的理解重商主义的政策的合理性,而且“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和机会,重商主义政策是在同样条件下达到从理性上讲可以辩护的目的的适当手段”[5]。
威廉·J·巴贝尔延续并扩展了1904年普莱斯(L L Price)所提出的“自由贸易是世界主义的,而保护是民族主义的”论断[9],他把重商主义的理论体系归纳为:(1)一个国家的对外账户应当受到调控,决不能听任看不见的手支配;(2)经济政策规划的优先性应当以国家财富而非各国的财富为中心两大理论前提,揭示了重商主义的理论核心正在于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之下,通过政府的干预政策机制推进国家财富的增长,传统经济理论所关注的贸易保护仅仅是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手段,而非理论体系的核心[1]。
重商主义与古典、新古典主义关于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的争论恰恰反映了其经济政策上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斯密所倡导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冲突,这也反映了17、18世纪,统一的国家政权在西欧的普遍建立,国家意识与国家利益概念的逐步确立,英国商人与之前垄断英国国际贸易的汉萨商人的冲突日益激化的背景下,民族意识得以抬头,利用政府的王权专制对于本国商人,本土利益实施保护性的干预,自然成为强大起来的专制王权争取经济支持的必然选择。这一时期日益昌盛的殖民掠夺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在激化新兴的英国,法国与在殖民地开拓中抢占先机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矛盾的同时,更进一步凸显了民族利益在争取全球市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的重要性。笔者认为,1598年汉萨商人被逐出英国市场正是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得以确立的标志之一,而重商主义在法国最为盛行的柯尔贝尔时期恰恰是法国中央极权体系最为强大,最为完整的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当政阶段也绝非偶然。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重商主义正是西欧民族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萌发结合的产物,其民族属性正是其区别于以往经济思想的关键所在。正如赫克歇尔所言“国家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主题和目标”[10],而把重商主义界定为“建立强权或国家的体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更将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正是重商主义创造了民族国家……要不然就是民族国家或孕育中的所谓民族国家在创造自己的同时,创造了重商主义”[11]。
马格努松把重商主义定义为一种适合于17、18世纪的“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主义”,其典型代表柯尔培尔体系的目标则是“由日益增强的国家经济控制手段来构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1],从而把重商主义与教条式的关于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区分开来。在他看来,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革命性突破在于广泛的讨论财富的创造、分配与消费,而在此之前,此类研究主题的讨论却并未出现。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国外经济理论学界更多地把重商主义界定为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家干预战略,而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贸易保护仅仅是这一战略思想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映射,或者说实现民族国家经济增长的具体的政策实践,其具体的政策内容也正是根据国内产业体系构建与国际竞争格局的演进而逐渐调整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西欧的建立与巩固,集权政府的战略目标也从规避国际竞争,保护本国市场,扶持本国幼稚产业成长转向争夺广阔的国际市场,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因此从严格禁止对外贸易转向追求贸易差额,从内敛式的封闭保守转向扩张式的殖民掠夺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并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思想的确立,从而为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国家垄断体制引起的贸易保护
17世纪,伴随着王权专制主义在西欧的普遍建立,处于封建等级金字塔顶端的国王开始谋求通过分等级的官僚机制以巩固自身的统治,通过有计划的利益分配,借助于卡特尔化的,垄断性的行业组织,与工商企业形成合谋,建立起国王、贵族和新兴的商人阶级,贸易商的联盟,并从具有明显垄断属性的获益人处获得更大额度的税收收入,推进权力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解决政府的财政压力,自然成为西欧各国的共同选择。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体制表现为一种“建立强权或国家的体制”(赫克歇尔),或者是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关于国家建构,确立国家特权的综合体系[12]。
随着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西欧王权专制通过向特定社会阶层,或特定人群出售,或者授予生产或销售特定商品的垄断特权,从而建立起以国家特权为核心的国家垄断体系。新兴的商人阶层,以及一些传统的行会组织,都可以以奉献重税为代价的方式,向王室寻租,以获得在特定经济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的排它性权利,特别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从事垄断性商业贸易的特权,广为人知的东印度公司正是这一垄断特权机制的缩影。
与后世的众多经济学专著不同,现存的绝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都是重商主义学者,更为准确的是,代表着特定经济利益的商人,或者官僚,向王室争取这种源自专制王权的国家垄断特权的产物。维纳直言“大量的重商主义文献由部分或全部、直白或隐晦地专门要求特殊经济利益的小册子构成。他们自己要求自由,但要限制其他人,这是重商主义小册子的商人作者们的立法计划的本质”[13]。
在重商主义政策体系下,由国家强制力所推行的专制垄断特权,以破坏商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为商人阶层谋求垄断利润,而此同时,在国内的产业组织体系中,由国家强制所有生产者加入城市行会,从而在一体化的指令下生产运营,把资本主义早期的手工业生产卡特尔化,进而形成封建王权与资本主义商业的联盟,而由进口禁令或保护性关税带来的贸易保护,则是保障国内商人或手工业者特权的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从这个方面而言,贸易保护只是17、18世纪以来,国家垄断主义持续积累的外在表现。
国家垄断特权的创设,极大的影响了以谷物和羊毛为代表的商品,以及纺织工人为代表的技术性劳动力在跨国配置,这也极大地促进了贸易保护政策在西欧的普及,再加上宗教战争愈演愈烈,完全打破了欧洲经济发展格局。如1581年,法王亨利三世强制命令所有法国工匠加入行会,执行行会规则,限定除巴黎和里昂之外的工匠必须留在所在的城镇,并强制维持质量标准,压抑市场竞争,限制生产与进口,完全消除了法国工业的流动性,迫使国内消费者为低质商品付出高昂代价,固然借助于越来越强大的垄断势力征得了更高的税收,也极大地降低了法国经济的活力,减慢了资本积累速度,制约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宗教战争对于胡格诺派工匠的杀戮,又为海峡对岸的英国提供了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反而带动了英国纺织产业的兴起。
而在英格兰,重商主义所倡导的在国内外贸易中的排它性的垄断特权表现得更加明显,在16世纪末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统治时期,这种国家垄断体制更是达到巅峰。宾多夫(S. T. Bindoff)将这一阶段描述为“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十年(1594—1603),几乎没有一种具有公共用途的物品——如煤炭、肥皂、淀粉、铁、皮革、书籍、葡萄酒、水果等等——不受到垄断权的影响”[14]。
民族意识的崛起,催生了面对不同国籍,不同阶层之间的歧视性政策,在强化政府对民族经济的干预的同时,更加速了垄断租金分配中的中央集权,进一步推动西欧各国政治体制的演进。中世纪以来,原羊毛始终是英格兰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到14世纪时,其年出口规模已经达到35 000袋[12]。但是其出口权长期垄断在以汉萨商人为代表的外国商人手中。为了筹措战争军费,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开始插手羊毛进出口贸易,以替国王征收羊毛税为条件,将羊毛出口的垄断权授予本国商人团体,从而将外国商人逐渐排挤出本国羊毛贸易领域,随手又进一步放松羊毛出口垄断权,将其授予由几百名商人组成的“商站商人公司”(Merchants of the Staple),借助这种出口中的垄断,商站商人公司一方面压低国内生产者的价格,另一方面又人为地抬高进口商价格,利用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剪刀差有效地补偿了向国王交纳的税收,与此同时,英格兰羊毛的年均出口量迅速降低到8000袋。
正如熊彼特所言,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欲望催生了重商主义理论,而源于商界和金融界的重商主义学者出于追求国家利益,特别是实现自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的考虑,提出了追求贸易差额的贸易保护观点。强权政治正是实现商界利益的保障,通过这种“海盗式的帝国主义”,强权和利润之间形成了的紧密的内在联系,二者之间固然可能存在着冲突,但是强权最终必将导致更多的利润[5]。正是由于重商主义盛行时期,各国普遍存在生产资料未被充分利用或未被充分开发的现象,才保证了贸易保护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合理性,而到了这些必要的限制条件逐渐消失时,重商主义的对外政策自然就从贸易保护转向更加自由(10)这一观点最早源于阿瑟·扬《英帝国现状政治论文集》(1772),此后维纳和熊彼特也继承了这一观点。详见《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四、对重商主义理论的误解根源
现代经济学对于重商主义的理解往往建立在其财富观与贸易观的基础之上,认为重商主义把财富与贵金属货币等同起来,并通过源于政府管制的贸易保护政策,获取贸易顺差,使得更多的金属货币流入,以此作为实现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因此保护主义才会被视为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一判断大约来源于17世纪初的早期重商主义者德·拉斐玛所主张的,金银是“王国和贵族的肌腱与支柱……是国家反对……敌人……的真正力量与物质基础”,由此保证货币更多地流入法兰西王国,实现国王从臣民处获得更多的货币,积累更多的财富和权力的最终目标[12]。然而,即使作为最为顽固的早期重商主义者,拉斐玛也并非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主张禁止货币的外流,相反,他主张允许金银自由流入流出,反对的是导致货币从法兰西王国流出,并流入外国人之手的商业贸易,由此来实现金银的净流入,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同一时期另一名重要的重商主义者,拉斐玛的政敌苏利公爵(the due de Sully)的确严厉禁止黄金白银出口,同时却批评拉斐玛对丝绸行业的保护,而倡导纺织品的自由进口,而成为这一时期“自由贸易者”的著名代表。两位官僚型学者尽管在财富观与贸易观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且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经济思想史中重商主义的理论原型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却同属早期重商主义的知名代表,这其实也是驳斥把重商主义标签化地等同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传统的事实依据。
实际上,把金银与财富等同起来只是早期重商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言的重金主义(Bullionisme),或者货币差额理论的基本特征,比如16世纪的老托马斯·史密斯,17世纪早期的托马斯·米勒斯和杰勒德·马林斯,他们都主张坚决禁止对外贸易和金银流出国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迅速增长的社会财富对于流通货币的巨大需求,以及金融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支撑作用。
在最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的名著《论英国东印度贸易:答对这项贸易的常见的各种反对意见》一书中,把金银等同于财富的偏见已经荡然不存,孟明确提出“财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的,国土本身的产物,另一种是人造的,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创造”[15],而把工业产品也纳入财富的范畴,因此,只要通过贸易出售多余产品,换回外国货币或者本国人民所需要的物品,就可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这也标志着重商主义从绝对禁止进口贸易的重金主义转向后期的贸易差额论。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把重商主义财富观简单归为金银就是财富的理论偏见,并不能客观地阐述重商主义学者共同的财富观与价值论。早在1677年,托巴斯·帕皮隆(Thomas Papillon)就在其出版的《东印度贸易是给这个王国带来最大利益的贸易》一书中阐述“固然衡量资本或财富的尺度通常是货币,但与其说这一尺度真的存在,还不如说它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拥有一万英镑的财产,尽管他手上可能连一百英镑都没有,如果他是个农民,他的财产就是土地、谷物或牲畜和农具……”[16]。
改良的重商主义学者尼古拉·巴尔本(11)无论从财富观,还是贸易观,巴尔本都与传统的重商主义思想截然不同,甚至是重商主义思想的重要的批评者,其倡导通过发展自由贸易来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因此更多被划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但是在一些文献中,也通常会把他纳入重商主义的改良派,或者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Nicholas Barbon)在论述贸易的重要意义时,把商品归纳为自然商品和人工商品两类,并将其视为一个国家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的财富,而“货币是一种工具,是商品的尺度,但不是白银。政府铸币的权威使之成为商业工具……”[17]巴尔本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清晰地界定了货币与金银之间的逻辑联系,指出“货币并不是绝对需要由金银制造,因为它唯一的价值是来自法律”[15]。而金银只是由于在防止伪造方面存在优势,才成为扮演货币角色的最佳选择,这样的观点不仅与传统理论中把金银与货币划等号的重商主义财富观完全不同,其实也已经很接近于马克思(Karl Marx)“金银天然是货币,而货币天然不是金银”的重要论断了(12)事实上,马克思的确受巴尔本影响颇深,《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多次引用巴尔本的论述,马克思对巴尔本极为推崇,对他评价为“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并把他和配第、孟德维尔、魁奈并提。。
熊彼特也认为,现代经济思想史中对于重商主义的理论,都建立在“必须假定‘重商主义’作家把财富与货币或金银‘财宝’看作是同一东西,或者假定他们把货币同货币可以购买的东西混淆在一起”的假设前提之上,而这一错觉恰恰源于“亚当·斯密不恰当地批评‘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而树立的坏榜样[5]。
在贸易观上,重商主义也从重金主义时代,完全否定国际贸易的合理性,到贸易差额论阶段,强调争取国际贸易顺差,谋求贵金属货币的净流入,再到晚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于自由贸易的倡导,经历了明显的从封闭到开放的演进过程,这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阶段,强调货币财富的积累,到帝国主义阶段突出国外市场开拓和加快殖民掠夺的自然演化。
值得强调的是,从帕皮隆,托马斯·孟,到蔡尔德,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很多都是东印度公司的代言人,其经济观点更多地建立在维护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其观点在早期更多的从国家垄断的角度强调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合理性,而后期的经济观点,更多是反驳重金主义的贸易保护思想,论证发展东印度贸易,特别是东印度公司进口亚洲商品的合理性,尽管其理论仍然建立在追求贸易差额的基础之上,但是其为贸易而辩护的政策主张,已经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西欧各国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就已经从利用贸易保护政策推动本国新兴产业崛起,逐渐向呼吁发展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自然演进过程。
重商主义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汇集了17世纪至18世纪以来几乎主要西欧社会活动家的经济,政治观点,但是除了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干预思想,无论在财富观、贸易观,或者货币思想上,不同学者之间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彼此之间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仅仅把早期重金主义的财富观视为整个重商主义的财富价值观,把重金主义贸易保护误认为重商主义一贯的传统,显然是不合适的。
五、结论
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之前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理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价值却长期为后人所遗忘,甚至其核心思想更多被人误解为贸易保护。事实上,重商主义所倡导的国家干预政策正是资本主义在西欧形成、壮大的根本原因。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不同需要,在民族利益至上的理论前提下,通过推行国家垄断主义,消除了中世纪的城市、乡镇与教会的分裂,才逐渐催生了统一的国际经济市场和现代资本主义全球经济。
重商主义思想的自然演化也正是当时全球经济从孤立分裂走向殖民化、全球化的映射,重金主义的顽固的贸易保护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而重商主义后期的贸易差额理论则为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殖民掠夺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从重商主义中分离出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更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次贷危机以来,封闭主义、本土主义思想重新抬头,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所引发的中美贸易争端更把这一思潮推向顶峰。有些学者将特朗普贸易保护简单地归结为新重商主义,其实正是把重商主义误解为保护主义的理论传统的真实映射。在当前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为追求制造业回归,所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其目标更多在于巩固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导地位,将其它国家长久固化于价值链低端,因而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攻击色彩,这一切与重商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基于幼稚产业扶持的临时性的被动防御政策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其产业政策的导向也是完全与美国当前服务经济的内在优势相悖,因而与其自身的经济增长的本质需要并不相符。
把现代全球经济中的贸易保护视为重商主义的回归,甚至界定为新重商主义的做法,实质上正是仅仅看到了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追求国家经济增长的硬核,这样的观点完全继承了斯密所建立的错误传统,从而将重商主义理论简单化、狭隘化和标签化,这也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巨大价值。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重新反思重商主义的理论价值,在新的历史阶段,把握民族国家经济成长中的国际策略,自然也就愈发重要了。
参考文献
[1]拉尔斯.马格努松. 重商主义经济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4-14,304.
[2]亚当.斯密,国富论[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475.
[3]VINER J. English theories of foreign trade before Adam Smi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0, 38(3): 249-301.
[4]HECKSCHER E F. Mtercanttilism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5.
[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14-549.
[6]COLEMAN D C. El Heckscher and the idea of mercantilism [J].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7, 5: 35.
[7]WILES R C. The development of mercantilist economic thought [M]. [S. l. : s. n.], 1987.
[8]SCHMOLLER G.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M]. New York: Van Rees Press, 1931: 50-51.
[9]PRICE L L. Economic theory and fiscal policy [J]. Economic Journal, 1904, 14: 314.
[10]HECKSCHER E F. Mtercanttilism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3.
[11]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601.
[12]默瑞·N·罗斯巴德.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44-376.
[13]VINER J.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37: 59.
[14]BINDOFF S T. Tudor England [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50: 228.
[15]托马斯·孟等. 贸易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6.
[16]HECKSCHER E F. Mtercanttilism [M].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3: 191.
[17]巴尔本. 论铸造新的更轻的货币——对洛克先生的《思考》的答复[A]. W·莱特温. 科学经济学的起源[C]. 纽约:道布尔迪出版社,1965:78-79。
【免责声明】《现代财经》微信公众平台所转载的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四、健康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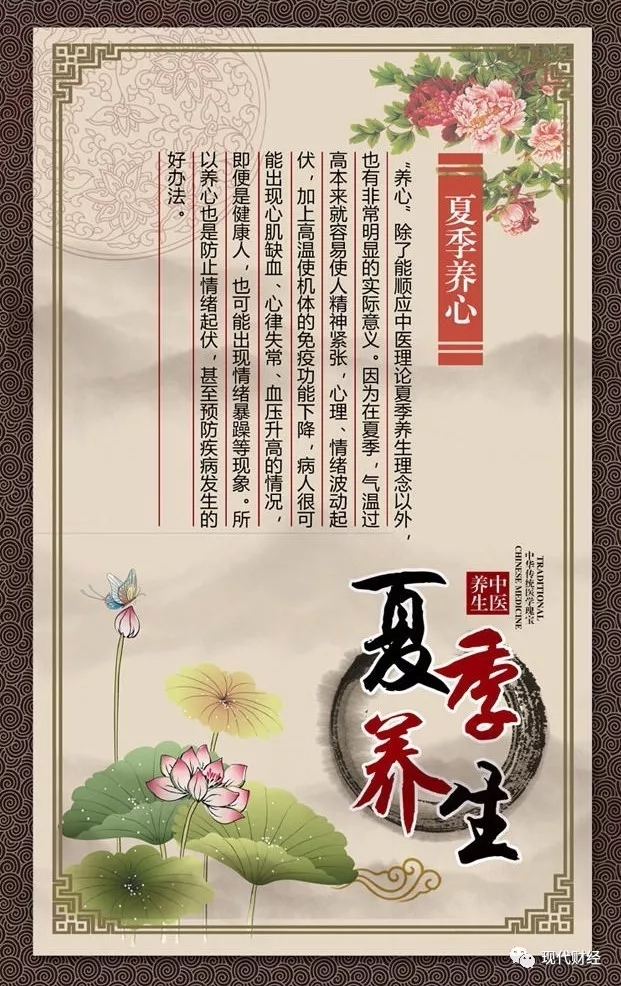
【面粉能洗净葡萄】葡萄去蒂放在水盆里,加入适量面粉,用手轻搅几下,然后将浑浊的面粉水倒掉,用清水冲净即可。
《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1299期)
编辑整理: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高阳、徐姗姗、王燕、姜倩雯 、王鹏丽、殷杰、李莉、郭蔷、许思宁、马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