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代际转移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吗?
代际转移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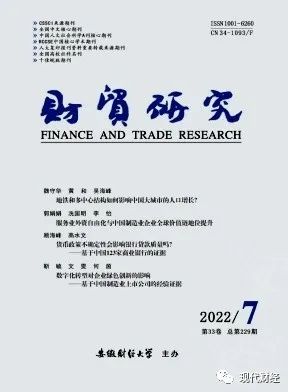
导读
摘要: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2017年的调查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对机会不平等的分解框架进行扩展,测算代际转移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代际传递现象明显;第二,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方向为正,代际转移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第三,由于代际传递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对整体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影响较高;第四,将不同年份的全效应贡献率和偏效应贡献率进行对比发现,全效应贡献率与偏效应贡献率相差不大,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占主导,间接影响的贡献较弱,代际转移是引致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代际转移;收入不平等;贡献率;
引用格式:李芳芝.代际转移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吗?[J].财贸研究,2022,33(06):26-35.DOI:10.19337/j.cnki.34-1093/f.2022.06.003.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更多的资源掌握在少数富人手里,穷人的发展机会受限,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古典自由主义公平观认为公平与否的判断标准是程序正义,而不是社会分配的结果。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个人能力不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是人们能够接受的,但是客观环境的不平等所引致的收入不平等却是大部分人所厌恶的。根据Roemer(1993,1998)对机会不平等的定义,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产生的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容易被人们接受,也体现收入差距存在的合理性;二是客观环境的不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主要包括性别、种族、出生地等个体特征和家庭禀赋、父代背景等代际转移因素,这种不受个人能力控制的客观环境导致的不平等即为机会不平等。根据“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收入不平等程度与代际收入弹性呈现正相关,表明代际转移程度越高的国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代际之间的收入转移是否也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代际转移是否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其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有多大?从代际转移视角审视收入不平等的深层次原因,对于缓解收入分配过程的机会不平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热点。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对收入分配关注的重点由分配结果是否平等的测度,转向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在此期间国外涌现出一些关于机会不平等的代表性成果,但主要围绕机会不平等进行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Arneson,1989,1990;Roemer,1993,1998)。21世纪以来,学者们的研究和关注重点集中在机会不平等的测度和定量分析上(Regina et al.,2013;Torche,2015;Roemer et al.,2016),并关注机会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Björklund et al.,2012;Ivanov,2014;Robert et al.,2020)。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使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从收入不平等指标中分解出机会不平等的贡献额。参数法的测算思路是将收入方程的变量分为客观环境变量集和个人努力变量集两大类,然后计算得到实际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指标和反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指标,两者的差额即为机会不平等;非参数法的测算思路是将个体分为若干群组,同一群组内个体的客观环境或努力因素相同,计算出的组间不平等指数即为机会不平等(Ferreira et al.,2011)。现有文献大都使用参数法进行测算,如Zhang et al.(2010)、史新杰等(2018)、汪晨等(2020)、孙枫等(2021)都使用该方法测算了机会不平等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参数法做了改进,如李莹等(2016)构建了更为全面的环境集和努力集,改进了机会不平等参数估计理论中对残差项的处理方式,以便更准确评判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引致程度;雷欣等(2018)和刘成奎等(2021)将收入模型中不可观测的环境和努力因素进行了量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收入估计方程的偏误。
虽然现有文献围绕收入不平等指标的分解及模型改进做了很大贡献,但大多只关注引致机会不平等的各种特征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大小,并没有实际测算出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同时,由于客观环境因素中的性别、种族、出生地等个体特征变量不受人为控制,而父代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等家庭禀赋特征对子代收入的传递主要体现了机会不平等,因此,代际转移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是人们更加关注的焦点。现有专门研究代际转移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文献较少。陈东等(2015)虽然选择了代际转移作为研究收入不平等的视角,但也仅仅是将父代的教育、职业、家庭收入等相关变量引入收入方程,通过父代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代际转移的作用效果,并不能确切反映代际转移程度的大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方鸣(2014)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的互动关系,没有深入探索代际转移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
综上,现有文献一方面关注反映机会不平等的特征变量这一整体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单独从代际转移视角对收入不平等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另一方面基于不同的参数或非参数分解方法对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分解,鲜有运用计量模型来充分论证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本文拟基于代际转移的视角,通过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计算代际转移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从代际转移视角为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新的证据和参考。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构建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省际面板回归模型,估计代际转移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方向和大小;第二,从客观环境因素中划分出代际转移因素集,对机会不平等的分解框架进行扩展,构建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贡献的扩展模型;第三,在测度代际转移时,克服了暂时性收入冲击和生命周期偏误对代际收入弹性指标的影响,通过测算各个省份不同年份的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反映省际代际转移的综合状况。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CGSS起始于2003年,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包含了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村/居民委员会,每年调查一万多户家庭的基本情况,调查项目涵盖被访者及其父母的收入情况、职业经历、教育水平等基本信息。本文研究的是省级层面的代际转移综合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比于其他同类型调查数据,其包含的省份数据更全面,目前该调查项目已公开2003—2017年共十年的调查数据。受下文测算收入代际转移所需调查变量的限制,选取2008—2017年的项目调查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问卷中个别年份样本量过少的省份删除,最终保留26个省份作为面板数据的截面维度。
(二)变量选择
代际转移和收入不平等同为综合性指标,构建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省际面板分析模型需要首先测算出各个省份的代际转移和收入不平等程度。
1.代际转移
学者们常用代际收入弹性测度收入的代际转移程度(Solon,1992;李力行 等,2015;邹薇 等,2019),但是Chetty et al.(2014)的经验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弹性具有不可避免的使用缺陷,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更能满足代际弹性指标的线性关系和稳定性。对于基于双对数收入方程的我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数据和估计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相差甚远,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有效克服模型中暂时性收入的冲击和生命周期偏误的问题。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使用排名—排名方程根据父代和子代在其所处时期永久收入的相应排名关系来反映父子收入代际转移状况。王伟同等(2019)将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的优势归结为对零收入或低收入人群的适用性、对收入观测年限不敏感从而产生较小的生命周期偏误、父子收入次序的显著线性关系等三个方面。基于此,本文采用收入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测算核心解释变量代际转移。为了充分体现父子代际收入的次序性,参考阳义南等(2015)和王伟同等(2019)的做法,使用自评的收入等级作为子代永久收入排名的代理变量,将14岁时的家庭收入等级作为反映父代收入次序的变量。这样处理一方面是因为在无法获取永久收入的现实情况下,自评的收入等级更能够反映个体在同时期人群中的相对排序,不受暂时性收入冲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14岁时的家庭收入等级更能体现父代中年时期的收入情况,一定程度上大大减弱了生命周期偏误的影响。
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可表示为:
Rankpi1=αp+βpRankpi0+εpi
(1)
其中:Rankpi1为p地区第i个家庭子代收入等级;Rankpi0为p地区第i个家庭父代的收入等级;αp为常数项;εpi为随机误差项;βp为p地区的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βp越大表示该地区的代际转移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
2.收入不平等
对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测度,经济学家一般使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衡量。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2)
其中,n是样本容量,yi和分别表示居民个人收入和均值,且y1≤y2≤…≤yn。
泰尔指数来源于广义熵指数。广义熵指数由信息熵导出,可表示为:
(3)
其中:n为样本容量,yi为该地区第i个居民的收入,为该地区居民平均收入;q为常量,q值越小,表示厌恶不平等程度越大。当q趋近于0时,称为泰尔第二指数,即:
(4)
当θ趋近于1时,则转化为泰尔指数,即:
(5)
3.其他控制变量
其一为城镇化水平。万广华(2013)和陆铭(2016)的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程度非常密切。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整体越高,进一步对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越大。本文采用各省份每年城镇户籍人口数占总户籍人口数的比例测度城镇化水平。
其二为教育支出占比。教育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石,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过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来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改善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通过计算各个省份的教育支出额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来反映各地对教育的投入和重视程度。
其三为开放程度。开放程度的提升能够通过增加投资机会进而缓和收入不平等状况。通过研究对外开放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发展经济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本文通过计算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该省份的开放程度,进而分析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其四为劳动报酬占比。Li et al.(2011)通过研究发现,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失衡是引致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主要因素。同时,劳动报酬收入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劳动报酬收入在收入分配过程中所占的比例大小会影响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收集各省份生产总值和劳动报酬数据来计算各省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
(三)描述统计
通过对26个省份2008—2017年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测算和整理,同时将收入变量按照2017年可比价进行消胀处理,得到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表1)。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2008—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表1中N为总样本量,n为维度,T为时间维度。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高于0.4则超出警戒线,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4462,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超出国际警戒线。收入的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均值为0.5049,说明部分地区的时间趋势波动明显,组内差距比组间差距相对要大;虽然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省份的代际转移指标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趋势,但代际间的收入传递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城镇化水平为0.5553,说明我国城镇化水平较高。对数化后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均值为1.0107,人均受教育年限大约为11年,说明教育仍旧是我国的国之大计,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格外重要。扶贫要扶智,素质教育程度影响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劳动报酬占比的均值为0.4701,说明劳动报酬收入仍然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代际转移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由于代际转移和收入不平等指标都属于综合性指标,研究居民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时,既要考虑变量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又要考虑时间的变化,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果。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解决遗漏个别解释变量所带来的偏差,同时可以克服代际转移和收入差距等综合性指标可能出现的样本量不足的问题,提高估计结果的精确度和可靠性。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本文使用的是2008—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截面维度大于时间维度,因此判定本文数据为短面板数据。HT检验通常作为短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方法,其原假设为:存在单位根。本文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统计量的结果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拒绝面板数据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面板数据满足平稳性的要求,适合进行回归建模分析。
(二)模型选择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主要有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三种形式,通过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表3)可以看出,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更优。
表3 模型选择检验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Yit=αi+βXit+uit
(6)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个体在第t时的取值,i=1,2,…,N,t=1,2,…,T;Xit为解释变量中第i个个体在第t时的取值;αi表示为对于i个个体有i个不同的截距项,其变化与Xit有关;β为回归系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其假定条件为E(uit|
αi,Xit)=0。
(三)回归结果
在构建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面板回归模型时,可能面临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有必要对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传统的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χ2值为0.09,P值为0.76,考虑异方差的DWH检验结果显示IV估计结果与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的差异也不显著,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构建的固定效应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核心解释变量为外生变量。但是由于本文所使用短面板数据的截面维度较大,变量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取值差异较大,因而可能存在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为了减弱回归估计过程中面板误差结构带来的偏误,本文使用面板校正标准误(下文简称PCSE)方法进行模型参数的估计。PCSE方法能够在保留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的基础上把残差项代入对角矩阵,并修正标准差,从而提高估计的有效性。同时,为了避免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使用逐步回归法将自变量逐步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注:***、**、*表示分别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2 =0.7386,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好。除劳动报酬占比之外,其他变量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结果符合预期。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方向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0.16,说明代际转移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尼系数大约增加16%,代际转移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快代际之间的流动,是缓解长期以来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根源。
城镇化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为-0.39,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基尼系数相应降低39%,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有效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教育支出占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负,说明提升公共教育支出将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开放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开放程度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在适度的条件下,适当限制开放程度将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情况;劳动报酬占比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在收入分配环节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占比,有利于降低现期的居民收入差距。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根据CGSS共选取了26个省份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由于无法满足时间上的连续性,一些省份(上海、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西以及重庆)的变量值在不同年份之间波动较大。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剔除以上省份,同时用泰尔指数替代基尼系数,基于19个省份2008—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PCSE估计法,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除了教育支出占比之外,其余变量都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影响,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好,P值显著。稳健性检验结果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正,代际转移在一定程度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表示分别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五、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分析
上文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验证了代际转移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不平等,代际流动现象的固化不利于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代际转移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呢?接下来基于贡献率的角度,测算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
(一)理论模型
根据Roemer(1988)构建的机会不平等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将影响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分为客观环境因素和主观努力因素。其中,客观环境因素主要指子代无法自己决定及改变的因素,包括子代个体的年龄、性别、婚姻、父母受教育水平及职业类型、家庭收入等;而主观努力因素主要是指子代可以自己选择而决定的因素,包括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工作类型等。原模型形式可表示为:
ln Wi=αCi+βEi+ui
(7)
其中,Wi表示子代个体收入,Ci表示客观环境因素变量,Ei表示主观努力因素变量,ui表示除了两种主要变量之外的不可观测部分及测量误差。
为了着重反映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将客观环境因素中子代无法控制的父代特征变量即家庭收入水平、父亲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分离出来作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代际转移客观环境变量C,其它子代客观环境变量如性别、年龄、婚姻等作为控制变量C0。由此把原模型扩展为:
ln Wi=αCi+β1Ei+β2C0i+ui
(8)
由于代际转移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部分主观努力因素变量,例如,子代无法改变父母的单位类型,但这些因素会影响子代未来的职业选择及受教育程度,因而将代际转移因素对主观努力变量的影响设置为:
Ei=BCi+εi
(9)
其中,矩阵B表示主观努力因素变量受到父代代际转移影响的程度。可将子代个体的收入函数表达式扩展为:
ln Wi=(α+Bβ1)Ci+β2C0i+β1εi+ui
(10)
其中:α表示父代代际转移因素对子代收入的直接影响,称其为“偏效应”;Bβ1为父代代际转移因素对子代收入的间接影响,称(α+Bβ1)为“全效应”。
测算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需要计算假设不存在代际转移时子代收入,即将代际转移客观环境变量的平均值代入收入函数。偏效应下的收入函数表达式和全效应下的收入函数表达式分别可以表示为:
(11)
(12)
根据式(11)和式(12)估算出反事实的子代个体收入,并计算出新的基尼系数,与样本的基尼系数进行比较,根据公式(13)计算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13)
其中,表示代际转移客观环境因素变量的均值,I(W)表示子代样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表示代际转移客观环境影响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由于收入函数的因变量为子代的个体收入,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2017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首先剔除个人年收入为0及高于50万元的样本,同时进行消胀和对数化处理。然后选取个体特征变量、父代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区域特征变量等作为子代收入函数的自变量。根据法律规定,18周岁为成年人,而大于49岁子代的父母无论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方面对子女的影响程度都较低,因此将子代的年龄控制在18~49岁,同时剔除所有变量中数据缺失及极端数据的样本。父代特征变量选取父亲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类型,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家庭特征变量选取家庭总人口数(居住在一起的)以及家庭全年总收入,剔除变量中家庭收入为0及高于100万元的异常值,并进行消胀和对数化处理。区域特征变量以地区变量(省份)为基础,依据我国经济区域划分标准将样本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四个经济区。
(三)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根据CGSS 2008—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中的个体收入数据,计算得到每年的样本基尼系数(见表6)。通过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年份实际基尼系数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差距较小,说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表6 2008—2017年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实际基尼系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其他指标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计算得出。
在对各年收入函数进行样本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反事实收入的估算,然后比较样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代际转移客观环境影响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根据式(13)分别计算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在偏效应和全效应下的贡献程度,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6测算的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偏效应和全效应贡献率可以看出,2008—2017年,我国由于代际传递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对整体收入不平等的直接贡献介于31%至43%之间,全效应贡献率与偏效应贡献率相差不大。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测算结果显示,长期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代际收入转移,优越的家庭背景为子代创造了良好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本,“拼爹”现象明显。同时通过将不同年份的全效应贡献率和偏效应贡献率进行对比发现,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占主导,间接影响贡献较弱,机会不平等是影响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消除代际转移固化现象便是一项强有力的举措。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2017年的调查数据,首先,克服暂时性收入冲击和生命周期偏误对代际收入弹性指标的影响,通过测算各个省份不同年份的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反映省际代际转移的综合状况,同时测算出省级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综合指标;其次,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估计代际转移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大小和方向;然后,对机会不平等的分解框架进行扩展,构建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贡献的扩展模型,计算代际转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收入不平等;最后得出研究结论,从代际转移视角为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新的证据和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测算2008—2017年我国26个省份的代际转移和基尼系数发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4462,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收入的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均值为0.5049,说明代际传递现象明显。
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方向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代际转移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尼系数大约增加21%,说明代际转移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第三,根据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测算结果,2008—2017年我国由于代际传递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对整体收入不平等的直接贡献介于31%至43%之间,不同年份间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都维持在30%以上。
第四,将不同年份的全效应贡献率和偏效应贡献率进行对比发现,全效应贡献率与偏效应贡献率相差不大,代际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占主导,间接影响贡献较弱,代际转移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缓解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本文基于机会不平等的角度研究发现,代际转移不仅体现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平等,而且是人们厌恶不平等的根源所在,从代际转移视角缓解收入不平等可以起到对症下药的效果。因此,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需要一个公平的机会和竞争机制,这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本身难以实现,需要政府部门在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改革和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时,保障每个社会成员享有相对公平的机会,防范代际转移固化对收入不平等的不利影响,实现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陈东,黄旭锋. 2015. 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不平等?基于代际转移的视角[J]. 经济评论(1):3-16.
方鸣. 2014. 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29):14-17.
雷欣,贾亚丽,龚锋. 2018. 机会不平等的衡量:参数测度法的应用与改进[J]. 统计研究(4):73-85.
李力行,周广肃. 2015. 家庭借贷约束、公共教育支出与社会流动性[J]. 经济学(季刊)(1):65-82.
李莹,吕光明. 2016. 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引致了我国城镇收入不平等[J]. 统计研究(8):63-72.
刘成奎,齐兴辉,任飞容. 2021.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经济与管理研究(2):95-110.
陆铭. 2016. 教育、城市与大国发展: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区域战略[J]. 学术月刊(1):75-86.
史新杰,卫龙宝,方师乐,等. 2018.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J]. 管理世界(3):27-37.
孙枫,张应良,李瑞琴. 2021.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基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的视角[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51-160.
万广华. 2013. 城镇化与不均等:分析方法和中国案例[J]. 经济研究(5):73-86.
汪晨,张彤进,万广华. 2020. 中国收入差距中的机会不均等[J]. 财贸经济(4):66-81.
王伟同,谢佳松,张玲. 2019. 中国区域与阶层代际流动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78-95.
阳义南,连玉君. 2015.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CGSS与CLDS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4):79-91.
邹薇,马占利. 2019. 家庭背景、代际传递与教育不平等[J]. 中国工业经济(2):80-98.
ARNESON R J. 1989. Equal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J]. Philosophical Studies,56(1):77-93.
ARNESON R J. 1990. Liberalism, distributive subjectivism,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J].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19(2):158-194.
BJÖRKLUND A,JNTTI M,ROEMER J E. 2012.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ong-run income in Sweden [J].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39(2/3):675-696.
CHETTY R,HENDREN N,KLINE P,et al. 2014.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9(4):1553-1623.
FERREIRA F,GIGNOUX J. 2011.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Latin America [J].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57(4):622-657.
IVANOV A. 2014.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the alignment of incentives [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53(3):16-25.
LI S,ZHAO R W. 2011. Special issue: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market reform and the widening of the income gap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32(2):140-158.
REGINA T R,TRÜBSWETTER P. 2013.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and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 [J]. Applied Economics,45(22):3183-3196.
ROBERT S,WANG M. 2020.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outcome inequality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30(11):1-23.
ROEMER J E. 1993. A pragmatic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galitarian planner [J].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22(2):146-166.
ROEMER J E. 1998.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EMER J E,TRANNOY A. 2016. Equality of opportunity:theory and measure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54(4):1288-1332.
SOLON G. 1992.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3):393-408.
TORCHE F. 2015.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56(3):343-371.
ZHANG Y,ERIKSSON T. 2010.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nine Chinese Provinces,1989~2006 [J].China Economic Review,21(4):607-616.
作者简介:李芳芝(1984--),女,安徽亳州人,经济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副教授。
【免责声明】《现代财经》微信公众平台所转载的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2393期)
编辑整理: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李莉、郭蔷、马洪梅、蔡跀、陈晨、张晓丹、白晓萌、李茸茸、梁晓娟、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