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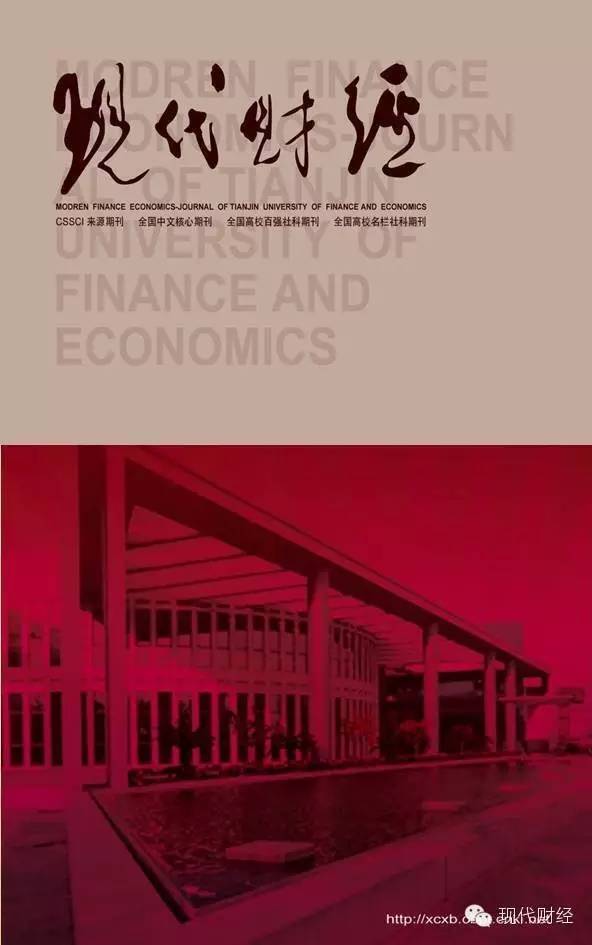
导读
摘要: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关键词:碳排放;碳达标;碳中和;数字经济;产业结构;
引用格式: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42(10):20-37.DOI:10.19559/j.cnki.12-1387.2022.10.002.
一、引言
在过去的4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也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1]。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做出了战略部署、明确了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已经增长到38.6%。在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支撑。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在加速实现“数实共生”,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向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治理、数字化生存等新生产、新管理、新生活方式全方位转型。
随着数字化在资源、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创新,数字技术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2]。在学术研究上,数字化和低碳化二者的关联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领域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当前需要探究的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是不是可以影响到碳中和碳达峰战略,如果确实有影响,背后的经济机制、效应又呈现什么特征?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关系是不是也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1)环境库兹涅茨假说(EKC)是指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环境污染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达到峰值或阈值后下降。?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事关我国两大发展战略的具体推动方式、路径和举措,对我国顺利达成两个百年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如期实现现代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部分学术文献提出数字经济可能会对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例如Li等(2021)[3]运用2005—2016年19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固定效应回归,研究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数字经济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支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但中国的数据是否也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还存在疑问。Li等(2021)[4]基于扩展的斯蒂尔帕特模型(STIRPAT model),利用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数字经济作为调节变量可以削弱能源结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但该文并没有直接考察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二者的因果关联。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典型模式,Guo等(2022)[5]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和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减排效果约为18.42个对数百分点,但该文忽略了产业结构升级所具备的内在推动作用。谢云飞(2022)[6]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但是考虑省内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运用省份宏观数据可能会遗漏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微观和中观影响机制和效应。总体来看,国内外在理论上详细阐释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学术文献较少,特别是涉及到准确评估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实证研究极为缺乏。为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需要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客观情况展开细致的实证研究。
从企业转型微观层面来看,数字化可以助力企业管理转型,实现碳排放的精准监测、计量和预测,科学规划能源消耗结构、提高执行效率,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减少碳排放。从产业发展中观层面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耗以及能源强度的影响方向,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但多数学者认同这样的判断:即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能源消费量和能源强度的重要因素[7],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8]。从能源供给等宏观层面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我国能源供给的网络化、集约化、精细化,并且通过数字化的能源生产、储能、传输、服务系统促进能源供给和消费相匹配,降低消费环节的能源消耗强度,催生新的低碳消费方式,大幅降低化石能源依赖度。
以上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可能是多路径、多维度的综合影响,目前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阐释这个问题。考虑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态,产业层面出现质和量的变化是数字经济转型最为典型的经济特征。而从绿色发展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既是各类经济投入与产出的“资源转换器”,又是各种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环境控制器”,故而产业结构的组合类型和调整强度直接决定了经济效益和能源利用效率[9]。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图从产业结构变动视角上构建一个理论框架研讨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机制和效应。具体来说,选取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继而影响碳排放这样的理论路径展开研究论证。
和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在三个方面存在边际贡献: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从多维角度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不仅探讨了内部作用机制,还评估了数字经济可能具有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相比已有研究,观察视角更为全面、理论维度更为丰满。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数字经济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本文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形成此种非线性关系的产业发展逻辑,还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第三,在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排放的机制研究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节能减排的作用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本文在实证研究中,不仅通过中介效应证实了产业结构升级确实能发挥正面作用,还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碳排放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碳排放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逐步扩大的,随着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开采和应用,大量二氧化碳被排放至大气层中,所以碳排放规模往往和工业化程度呈现高度相关。据统计,1960年以来,全球碳排放强度呈现稳定下降趋势,但人均碳排放量仍稳步上升。当今世界已进入以数据赋能、万物互联、智能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本质上是由于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内生驱动的。在数字经济时代,碳排放和经济形态呈现出何种关系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很可能正是人类未来解决能源和矿产资源利用与生产生活需求矛盾的关键所在[2]。
数字技术与碳排放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创新,必然会对我国碳中和碳达峰战略产生深远影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仅推动碳减排的“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碳减排的“间接效应”。同时,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重工业特征的信息产业可能加大能源消耗,因此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碳排放可能具有反向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另外,相关文献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网络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空间的相关经济变量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10],理论上,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也可能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一)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机制
已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动能。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构成了数字经济的主要经济环境[11],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可以颠覆企业盈利模式、改变市场结构、扩展资源配置的边界[12],从而能推动以劳动密集型、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技术含量高、环境友好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转移,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驱动力[13]。第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数字经济促进创新的功能已经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可。Varian(2010)[14]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网络的组成部件是数字字节、编程语言、协议、标准、软件库、生产力工具等,网络创新不需要库存管理,也没有运输延误,创新者可以联合起来创建新的web应用程序,这种平行发展引起了全球网络创新的爆发。而创新效率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创新效率通过产业生产是否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来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这是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实现来达到生产的潜力边界[15]。其次,在创业影响方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市场规模、知识溢出和要素组合等培育更多的创业机会,也会从加快信息交互和思想传播等途径丰富创业资源,从而促进城市的创业活跃度[16]。相关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对于城市和农村创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例如网络众筹等新型融资方式可以帮助创业者用更加低的成本获得更大范围的融资支持[17];这些全新的数字金融模式相比传统金融资金配置效率更为显著,更有利于满足中小创企业信息获取需求和带来城乡居民创业机会的均等化[18-19]。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同时也会探索出产业发展的新内涵、新空间和新领域[20]。第三,数字经济对不同行业的差别渗透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在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前景,能通过加速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的流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21]。其次,零售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是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中的领域之一[22];大数据也可以和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促使传统制造业更有效率地实现资源配置,更加精准地组织采购、生产、营销、物流等经营活动[23],并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错配及促进创新来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率[24]。但数字经济对农业渗透则相对滞后。一方面,基础设施城乡异质性将导致数字经济对第一产业的深度渗透速度低于第二、三产业。另一方面,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数字化资本将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25]。
对于实现节能减排的战略目标,已经形成共识的三大路径是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其中,能源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正面作用学界基本没有争议,但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尚未形成共识。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很小,甚至存在负面影响。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各产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即产业能耗强度的降低,结构效应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26]。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城市的碳减排[27-28]。王文举和向其风(2014)[7]通过构建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对实现中国阶段性碳强度目标的贡献度可能会达到60%左右。笔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并不仅仅表现为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或工业部门产值的降低,而是由于制造业内部技术升级,带动生产率提升,从而推动工业结构内部调整而逐步演化为三次产业外部产值比例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动。产业结构升级实质是资源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使得效率高的产业部门比例持续增加,最终引致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共同提高[9]。因此,产业结构升级总体上来看还是由于技术创新和突破而内生的,本质上是有利于我国城市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实现碳减排的,我国特定时期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负面影响是一种短期现象,并不是长期性发展规律。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H1 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的碳减排产生正面作用。
(二)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下,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向外拓展,已经由最初的数字产业化过渡至产业数字化,涉及的行业由电子信息制造、基础电信、软件工程等信息产业进一步延伸至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其他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首先,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即数字产业化阶段,一方面,电信产业的发展表面看似不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其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的研发,并不像传统制造业依靠煤炭、石油、森林等生态资源的大量投入,但其依赖的硬件制造—电子元器件、设备和整机生产等却都属于高耗能环节,会增加碳排放。另一方面,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业等数字经济产业,电力密集程度较高,大约占到了全球发电量的 10%[2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字经济的聚集性较强,数据的储存、传输和处理均都需要数据中心的支持,所以往往在很小的空间里有着非常密集的设备设施投入,比如大型的数据中心或者超级计算机等,这些设施设备的运行都需要耗用大量的电能[30]。据研究测算,全球数据中心加起来,电力消耗总量已经占据了全球电力年使用量3%(2)数据来源:《全球信息社会蓝皮书: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21)》。https://www.pishu.cn/zxzx/xwdt/574296.shtml。。2018 年我国数据中心总耗电约1 600亿千瓦时,相当于整个三峡水电站全年发电量[31]。可见,在数字化技术还局限在信息产业内部的产业数字化阶段。由于信息制造产业和数据中心等的高耗能特征,在能源结构和效率未得到技术改善的前提下,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刺激高耗能,并加大碳排放产生。2022年2月我国启动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东数西算工程,原因之一也在于数据中心耗能较高,东部热点区域所承受的压力逐步显现,而西部地区的光伏、风电、水电等绿色能源丰富,有利于提升数据中心绿色能源利用比例,减少火电和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有助于国内整体的节能减排。2000—2017年26个欧洲国家的经验数据也显示,绿色ICT基础设施对于可持续生产、消费,以及通过清洁生产技术和环境法规等措施保护气候变化是至关重要的[32]。
其次,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成长期,即产业数字化阶段,数字化技术扩散到非信息化产业,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这些行业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从而提升其能源配置效率。特别地,随着数据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在资源、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创新,以智能传感、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可以重塑能源系统。数字技术在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3)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指的是一个人或者团体的“碳耗用量”。、碳汇(Carbon Sink)(4)碳汇(Carbon Sink)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可以促进能源行业的数字化监测、排放精准计量与预测、规划与实施效率提升,从而大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直接或间接减少能源行业碳排放量[33]。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对自然和地理条件的精确三维建模,缩短清洁能源的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效率[34]。
再次,随着数字技术在传统行业和能源行业的深入应用,利润获取方面取得比较优势,将会激励其不断提升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当数字技术创新的能源边际溢出效率超过数字经济发展新增能源消耗,产业碳排放量就会达到一个拐点。同时,能源规划、检测、控制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能够反作用于传统的非信息产业,促进数字产业化出现绿色发展的新动力、新模式,从而大幅减少能源消耗,减少碳足迹。据统计,能源、制造、农业和土地利用、建筑、服务、交通和其他领域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已经可以帮助减少15%的全球碳排放[35]。绿色经济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将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数字化的循环互动和螺旋发展共同推动了碳排放“倒U型”传导机制的形成。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层面来看,也可以得出类似的规律,例如Li等(2021)[3]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引入索洛增长模型,发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企业会重新配置生产设备,增加产量,从而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企业产量稳定,数字化技术会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H2 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研究假设1,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Carbon-Eit=α0+α1Digitalit+α2Zit+λi+ηt+εit
(1)
Indus-Sit=α3+α4Digitalit+α5Zit+λi+ηt+εit
(2)
Carbon-Eit=α6+α7Digitalit+α8Indus-Sit+α9Zit+λi+ηt+εit
(3)
式(1)中,Carbon-Ei,t为城市i在t时期的城市碳排放水平,Digitali,t为城市i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向量Z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λi为城市固定效应,η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除了式(1)所体现的直接效应,为讨论产业结构变动是否为二者之间的中介机制。设计的检验步骤如下: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ital对于碳排放Carbon-E的线性回归模型式(1)的系数α1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分别构建Digital对于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变动Indus-S的线性回归方程式(2),以及Digital与中介变量Indus-S对Carbon-E的回归方程式(3),通过α4、α7和α8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表1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核心解释变量
学界在衡量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指标上,目前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运用互联网平台机构或信息化研究机构,运用大数据采集编制数字化发展指数来衡量。二是用互联网普及率、网站数、CN域名数等单一指标来衡量。三是根据信息产业、电信业务、电子商务和企业数字化等数字化指标构建指标权重的方法进行综合衡量。总体来看,第一种方法主要聚焦于数字产业化领域,可能并不能覆盖所有的数字经济产业,衡量方法上科学性稍显不足。第二种方法设置的指标覆盖维度相对较为有限,因此用这两种方法来衡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借鉴黄慧群等(2019)[24]、赵涛等(2021)[16]的做法,运用第三种指数构造法,将互联网发展作为测度核心,并加入数字交易的指标体系,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方面对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来说: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采用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四个方面的指标。数字普惠金融运用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代理指标。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以上5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后降维处理,最终得到我国各地级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表1是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和测量方法。
2.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并根据吴建新和郭智勇(2016)[36]的方法汇总计算出城市层面的碳排放数据,单位为百万吨。
3.中介变量
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是用非农产业的比重、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Moore结构变动指数、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等指标来衡量[15]。本文使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第一个产业结构升级指标(Indus-S1)。另外借鉴徐敏和姜勇(2015)[37]的方法,将第一、二、三产业囊括在内,构造第二个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dus-S2)作稳健性检验,测算公式为
(4)
其中,qi为第i产业的产值比重。
4.控制变量
为了较为精准地评估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全面影响,减少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尽可能控制了会影响城市碳排放的相关经济发展变量,具体设置如下:(1)经济发展速度(E-Grow),用该城市每年的GDP增长速度表示;(2)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人均GDP来表征;(3)财政收入水平(Fiscal),以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表示;(4)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以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比GDP来表示;(5)人口规模(Lnpopu),通过该城市年末人口规模来刻画;(6)政策变量(Test),考虑到我国在样本考察期内先后实施了三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了控制其政策影响,这里将试点城市作为虚拟变量进行控制;(7)行政区域土地面积(Area),以当地城市区划的土地面积(平方公里)来表示。同时,为了减缓异方差对于方程估计的不利影响,对于以绝对量数据形式存在的控制变量采取了对数化处理。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作为研究基础,最终形成了2 493个城市均衡面板数据(5)删除了毕节、铜仁等存在缺失值的地级市数据。。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和相关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部分地级市统计年报。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可以发现,碳排放指标(Carbon-E)的均值为9.032 1,最小值为0.116 0,最大值为228.611 9,标准差为15.079 6,表明我国不同城市间碳排放存在较大的差距。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Digital)、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dus-S)同样也表现为“标准差大、均值小”的特点。在控制变量方面,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速度(E-Grow)、经济发展水平(LnP-gdp)、财政收入水平(Fiscal)、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以及人口规模(Lnpopu)等数据方面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这表明我国不同城市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四、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作用
(一)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3报告了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线性估计结果。在列(1)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Digital)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确实能够促进城市实现碳减排。列(2)和列(3)显示了数字经济是否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结构(Indus-S1和Indus-S2)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中介变量(Indus-S1和Indus-S2)依次放回到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回归方程中,列(4)和列(5)中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系数相比列(1)都有所下降,而且产业结构升级指标(Indus-S1和Indus-S2)也都显著为负。依据系数判定法,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确实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作用机制,该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
表3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过的t 值或z 值。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基本结论的稳健和有效,本文分别采用更换模型估计方法、变换样本范围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更换模型估计方法
上文的模型为静态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城市碳排放可能会受到上一年碳排放的动态影响,为了缓解这方面的估计偏误,在模型中加入了上一年的碳排放变量,通过设立动态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估计。表4列(1)的结果表明,回归结果保持稳健,但数字经济的系数绝对值明显变小,同时滞后一期的碳排放指标显著为正,说明城市碳排放确实受到了上一年的动态影响。
2.控制宏观政策环境
由于各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存在不同,为了保证估计的全面和稳健,缓解省份宏观政策环境的影响效应,本文又额外控制了省份变量以及省份与年份交叉的时间趋势项。表4列(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省份宏观环境后,除了回归系数和t值有显微变动,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碳排放影响的显著性都未发生实质变化。
表4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识别不足检验指的是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内数字为P值。弱工具变量检验指的是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内数字为15%的显著性水平。
3.内生性的处理
第一,控制变量集可能并没有完全覆盖影响城市碳排放的所有经济因素;第二,城市的碳排放可能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企业家可能优先选择碳排放较少、环境质量较高的城市进行数字产业的布局。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本文关心的因果关系可能具有内生性问题。为了避免模型不发生偏误性估计,对方程进行了DWH检验,发现p值小于0.05,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符合内生解释变量的特征。借鉴黄群慧等(2019)[24]和赵涛等(2021)[16]的做法,构建样本城市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与1984年各城市每万人电话机数量构造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并对方程进行了系统GMM估计,删去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共计224个样本。
表4列(3)的结果表明,在运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后,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碳减排的正面效应仍旧成立,结果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此外,对于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检验,Kleibergen-Paaprk的LM统计量p值均为0.00,显著拒绝原假设;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Kleibergen-Paaprk的Wald F统计量也都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也并不存在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显示出较好的有效性特征,选取历史上各城市电话机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投资规模的交叉项作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
鉴于合成工具变量(Bartik instrument)在“相关性”和“排他性”两个标准中展现出的优良特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多有运用,本文尝试构造了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合成工具变量(Bartik instrument),并构建GMM(IV+2SLS)方程进行回归,表4列(4)显示,通过2SLS第一阶段回归,合成工具变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可以认为合成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的要求;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如表4列(5)所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与城市碳排放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并且F统计量大于10,据此可判断该工具变量不存在弱相关问题,满足外生性假定。
综合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在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城市碳减排的基本结论依然是成立的,这表明在现阶段,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促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五、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
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部分,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的溢出效应,本节验证此假设。
表5 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首先,在式(1)的自变量中加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初步确认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验证了研究假设2。
其次,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检验,设定面板门槛模型如下
Carbon-Eit=β0+β1Digitalit×I(Digitalit≤θ)+β1Digitalit×I(Digitalit>θ)+β2Zit+εit
(5)
其中,Digitalit既是核心解释变量也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变量,I(·)为取值1或0的指示函数,满足括号内条件即为1,否则为0。式(5)考虑的是单门槛情形,可以根据样本数据的计量检验等步骤扩充至多门槛情形。笔者对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Digital)依次进行了三重门槛、双重门槛和单一门槛的存在性检验,运用boorstrap自助法反复抽样500次后,结果通过了单一门槛,但未通过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从表5列(2)(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加不加入控制变量,方程单一门槛效应都是显著的,门槛值为5.651 2。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增加了碳排放;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的时候,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抑制了碳排放。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确实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特征,从而也就证实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数字经济之间同样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
进一步,笔者将产业结构升级指标(Indus-S1和Indus-S2)设为门槛调节变量,都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表5列(4)(5)门槛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门槛调节变量(Indus-S1和Indus-S2)呈现出和数字经济门槛变量相同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并且门槛值(5.451 2和5.436 7)明显降低,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会对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非线性溢出效应产生间接作用,而且可以促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这个实证结论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确实是有利于我国城市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六、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
我国城市之间由于资源禀赋、政策背景、市场发育等原因,发展程度出现了分化,为了细致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不同类型城市碳排放的差别影响,本文对于城市样本进行了分类,尝试从区位、规模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来说:一是按照所处区域将城市样本归类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二是按照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标准(6)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提出的城市划分标准,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市归类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城市常住人口依据住建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20》统计数据为准。,按城区常住人口将城市样本归类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类。
首先对异质性城市的碳排放数据和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6。可以发现:(1)在城市碳排放规模(百万吨)指标上,东部城市的碳排放规模明显要大于中西部地区城市,而中部城市虽然整体上大于西部城市,但与西部城市的差距不是特别明显。从城市规模来看,无论是均值或是中位数,大中小城市碳排放量都呈现较为明显的规模差距。可见,目前我国城市碳排放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城市和大城市,碳排放量主要还是和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相关的。(2)从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来看,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要领先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城市要高于西部地区城市,但中西部城市差距不是很大;从城市规模来看,大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小城市呈现较为明显的发展差距。总体来看,东部城市和大城市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先发优势”。以上描述性统计结果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排放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6 各类城市的碳排放和数字经济发展差异
从表7列(1)-(6)可以看出:(1)我国东部、规模大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都显著为负,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东部和规模大的城市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已经基本处于倒U型拐点的右侧,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提升产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可以逐步减少城市的碳排放。(2)我国中部、规模中等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这两类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好处于倒U型拐点附近,目前还未有效迈过拐点,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减排效应一定程度上还未能抵消数字产业化阶段积累的碳排放量。(3)我国西部、小规模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主要原因在于这两类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目前都处于倒U型拐点的左侧,在此数字产业化阶段,电子元器件、设备和整机生产等高耗能信息产业会导致碳排放显著增加。
以上异质性分析实际上验证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碳排放确实存在倒U型的非线型关系,各类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其碳排放水平处于倒U型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东部和大城市进一步实现碳减排,也有利于中西部和中小规模城市尽快迈过倒U型拐点,进而有利于我国城市从整体上迈入低碳绿色发展路径。
表7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七、拓展性研究
随着空间计量理论和实证方法的发展,近年来关注经济变量空间溢出效应的学术文献逐渐增多。从理论层面来看,经济要素在某一空间区域的发展演变既有可能产生分散效应,即通过资源、信息、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在溢出范围内促进区域空间内部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从而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也有可能产生集聚或极化作用,即利用先发优势吸引甚至攫取周边地区的要素资源,导致区域空间内部不平衡加剧,由此带来了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学者们在实证研究层面,由于考察的视角、时期、数据以及估计方法的差异,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研究结论。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或电子商务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8]。但也有相反结论,例如Yilmaz等(2010)[39]通过分析美国48 个州的面板数据后认为,一个州或地区可以通过通讯基础设施的投资获益,但其他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地理的邻近扩大了负向溢出效应,总体的溢出效应表现为负。相关学者发现,在中国具体情境下互联网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可能会导致地区间的资源错配[40]。在能源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区域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作用,并且这种空间溢出作用在逐渐增强,同时,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作用具有显著的影响[41-42]。徐维详等(2022)[43]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并且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 100 km处外溢达到峰值。但我国也有学者发现如果从生态效率角度来观察,当邻近范围为150 km时我国城市主要受到邻近生态效率较低城市的负向空间溢出影响[44]。
考虑到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差异,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相应的作用方向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为此,本文在式(1)中引入此二者的空间交互项,进一步将其拓展为一般形式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Indexit=γ0+ρWIndexit+φWDigitalit+γ1Digitalit+γ2Zit+uit
(6)
uit=λWuit+εit
(7)
其中,ρ代表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Z为控制变量集,u为干扰项,φ为核心解释变量空间交互项的弹性系数。空间权重矩阵具体采用了反地理距离面板数据。笔者首先运用Moran’s I指数检验了反地理距离矩阵下城市碳排放和数字经济发展各年度的空间自相关性,结果见表8。可以看出,2011-2019年城市碳排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Moran’s I指数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2011-2017年我国各城市的碳排放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聚性质。
表8 2011-2019年城市碳排放和数字经济的空间自相关性
表9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空间模型的回归结果
通过Hausman检验,上文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时空双向固定效应较为合适,表9分别列示了SAR、SEM、SAC和SDM 四种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四种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都显著为正,其中,SDM模型数字经济的空间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这就初步表明各地级市在空间上不仅存在外生的数字经济交互效应,城市碳排放之间也存在内生交互影响。
由于不同类型的空间计量模型所假定的空间传导机制是不同的[45],笔者继续运用Wald检验和LR检验对上述四类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SDM模型为较优选择。在SDM模型中,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项和空间交互项对城市碳排放都有显著影响,但SDM模型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并不能直接用来反映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边际影响,需要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才能具体显示出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偏微分影响。进一步在SDM模型回归中加入效应显示命令(effect),结果见表10。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城市碳排放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都显著为负,这就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对周边城市碳排放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徐维详等(2022)[43]认为基础设施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原因。从本文关心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视角来看,产业转移往往发生在相邻地区之间,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可以通过高效的信息传递压缩时空距离,增强区域间经济活动关联的广度和深度[16]。基于此种原因,数字经济发展很可能提升了较发达地区向周边地区进行产业扩散的规模和速度,从而带动相邻地区产业结构的跳跃式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是能够相应减少城市碳排放的,这也是本文机制分析部分主要发现之一。
表10 SDM模型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
八、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碳减排的特征事实,运用2011—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视角,综合采取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空间效应模型,多角度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内在机制和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城市碳减排,有力支撑了我国碳中和碳达峰行动,在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以及控制省份宏观政策环境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是成立的。(2)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非线性特征,证实了中国情境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的成立,这和数字经济发展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规律是相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作为调节变量能够形成门槛效应,表明在城市低碳生态发展系统中,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和数字经济形成合力共同助力城市达成碳中和碳达峰行动。(3)我国东部主要城市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市已经迈过数字经济发展的门槛值,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但大部分中西部和中小人口规模的城市还处于倒U型左侧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碳排放。(4)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碳减排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城市碳排放会受到本市和周边城市数字经济活动的加权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1)继续加强碳中和碳达峰领域内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开拓。综合探索和运用大数据、AI、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技术监测能源生产、供给、交易、消费过程,建立各产业碳排放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2)继续加快数字化碳中和管理技术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中的融合应用。尤其要注重提高数字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目前处于数字产业化发展阶段的相关省份,注意采取诸如“ICT基础设施绿色化”等对冲措施,避免通信基站、数据中心等产生过多的碳排放。(3)综合采取财政、金融、人力资本提升等多种公共政策手段,促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特别是资源型省份应摒弃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增长路径,限制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的发展,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4)继续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在城市区域间配置的空间均衡,加密地域间的网络连接维度,叠加运用行政手段和市场力量激励数据资源、数据要素跨地区交易、配置,对区域空间内部碳排放的数字化协作要进行总体规划、详细论证、周密执行。
参考文献
[1]IRFAN M, ELAVARASAN R M, YU H, et al. An assessment of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utilize solar energy in China: end-user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92(2):126008.
[2]陈晓红,胡东滨,曹文治,等.数字技术助推我国能源行业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路径探析[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36(9):1019-1029.
[3]LI X Y, LIU J, NI P J.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O2 emissions: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 Sustainability,2021,13(13): 7267.
[4]LI Y, YANG X D, RAN Q Y, et al. Energy structure, digital economy, and carbon emissions:evidence from China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1, 28(45): 64606-64629.
[5]GUO Q B, WANG Y, DONG X B. Effect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on energy saving and CO2 emission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Applied Energy, 2022, 313(5): 118879.
[6]谢云飞.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J].当代经济管理,2022,44(2):68-78.
[7]王文举,向其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其节能减排潜力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4(1):44-56.
[8]李治国,车帅,王杰.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中国275个城市的异质性检验[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178(5):27-40.
[9]于斌斌.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提高地区能源效率?——基于幅度与质量双维度的实证考察[J].财经研究,2017,422(1):86-97.
[10]李天籽,王伟.网络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比较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264(12):5-12.
[11]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9,242(2):66-73.
[12]杨新铭.数字经济:传统经济深度转型的经济学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66(4):101-104.
[13]陈晓东,杨晓霞.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灰关联熵与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J].改革,2021,325(3):26-39.
[14]VARIAN H R. Computer mediated transac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2):1-10.
[15]付宏,毛蕴诗,宋来胜.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3,306(9):56-68.
[16]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17]MOLLICK E R, KUPPUSWAMY V.After the campaign: outcomes of crowdfunding [J]. UNC Kenan-Flagler Research Paper, 2014, 2376997(1):1-18.
[18]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70(4):1557-1580.
[19]何宗樾,宋旭光.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J].财贸经济,2020,41(8):65-79.
[20]张于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思路与主要任务[J].经济纵横,2018,394(9):85-91.
[21]郭凯明.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J].管理世界,2019,35(7):60-77+202-203.
[22]谢莉娟,庄逸群.互联网和数字化情境中的零售新机制——马克思流通理论启示与案例分析[J].财贸经济,2019,40(3):84-100.
[23]李辉.大数据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实践基础与政策选择[J].经济学家,2019,243(3):52-59.
[24]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377(8):5-23.
[25]陈小辉,张红伟,吴永超.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产业结构水平?[J].证券市场导报,2020(7):20-29.
[26]林伯强,杜克锐.理解中国能源强度的变化:一个综合的分解框架[J].世界经济,2014,428(4):69-87.
[27]于左,孔宪丽.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J].财贸经济,2011,355(6):129-135.
[28]朱永彬,刘昌新,王铮,等.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及其减排潜力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3,266(2):35-42.
[29]WILLIAMS 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J]. Nature, 2011, 479(7373): 354-358.
[30]HITTINGER E, JARAMILLO P. Internet of things: energy boon or bane? [J]. Science, 2019, 364(6438):326-328.
[31]洪竞科,李沅潮,蔡伟光.多情景视角下的中国碳达峰路径模拟——基于RIC-LEAP模型[J].资源科学,2021,43(4):639-651.
[32]ANSER M K,AHMAD M,KHAN M A,et al.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mitigating carbon emissions: evidence from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1,28(17): 21065-21084.
[33]巢清尘.“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科学内涵及我国的政策措施[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1,706(2):14-19.
[34]ALLAM Z, JONES D. Future (post-COVID) digital, smart and sustainable cities in the wake of 6G: Digital twins, immersive realities and new urban economies [J]. Land Use Policy,2021,101(2): 105201.
[35]Exponential Roadmap. Exponential roadmap 2030[EB/OL], [2020-03-01]. https://exponentialroadmap.org/exponential-roadmap/.
[36]吴建新,郭智勇.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J].统计研究,2016,33(1):54-60.
[37]徐敏,姜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32(3):3-21.
[38]张俊英,郭凯歌,唐红涛.电子商务发展、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19,372(3):105-118.
[39]YILMAZ S, HAYNES K E, DINC M. Geographic and network neighbors: spillover effects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0,42(2): 339-360.
[40]韩长根,张力.互联网是否改善了中国的资源错配——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19,449(12):43-55.
[41]胡彩梅,付伟,韦福雷.中国省域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204(8):938-942.
[42]潘雄锋,杨越,张维维.我国区域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4,109(4):132-136+186.
[43]徐维祥,周建平,刘程军.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J].地理研究,2022,41(1):111-129.
[44]黄建欢,方霞,黄必红.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空间溢出的驱动机制:见贤思齐VS见劣自缓[J].中国软科学,2018,327(3):97-109.
[45]白俊红,王钺,蒋伏心,等.研发要素流动、空间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7,598(7):109-123.
【免责声明】《现代财经》微信公众平台所转载的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2433期)
编辑整理: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陈晨、张晓丹、白晓萌、李茸茸、梁晓娟、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