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财经期刊佳作关注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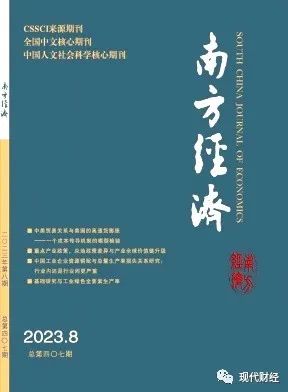
导读
摘要: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关键词:数字经济;阶层向上流动;中等收入群体;共同富裕; 引用格式:田艳平,向雪风.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J].南方经济,2023(04):44-62.DOI:10.19592/j.cnki.scje.400225.
一、引言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提速增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实现了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收入分配状况也得到改善。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8,相较于2008 年的0.491 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0.4 的国际警戒线,过大的收入差距成为了阻碍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2 万元,已经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不同群体来看,2014 年到2020 年收入最高的20%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93 万元,而收入最低的20%群体仅增加了0.32万元,收入增长悬殊会导致收入结构进一步恶化。截至2020年,中间20%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 万元,低于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家庭划分区间的下限①国家统计局将2018年价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这意味着到2020 年我国仍有超过60%的人群未达到中等收入标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显著改善分配结构,到二〇三五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在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十三五”期间,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光纤用户占比超过94%,推动移动互联网普及,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108%,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政府的建设①数据来源于国务院2021年12月12日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总规模达到了3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6%,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十四五”期间,还要实现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继续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图1 不同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
图2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数字经济的普惠共享是否能够缓解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促进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各收入阶层群体特征,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相对于静态的收入阶层划分,本文从收入阶层动态流动的角度分析各收入阶层的群体特征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第二,本文以收入阶层流动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为切入点,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证;第三,基于分析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受阻的原因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数字经济促进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内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补充了现有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已有关于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阶层流动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考虑到阶层向上流动主要由家庭收入增长引起,本文从中等收入群体划分与扩容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影响三方面进行相关文献回顾。
在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方面,经常使用的是相对收入标准和绝对收入标准。关于相对收入阶层的划分一般基于中位数或中位数的倍数,例如Pressman(2010)和Grabka et al.(2016)分别将中位数收入的75%-125%和67%-200%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在绝对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上,Mila⁃novic and Yitzhaki.(2001)以巴西平均收入为下限,意大利平均收入为上限,认为人均日收入介于12-50美元之间可被界定为中产阶级;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等(2012)、李强、徐玲(2017)和刘志国、刘慧哲(2021)分别将年平均收入介于2.2万-6.5万、3.5万-12万和2.85万-11.77万之间的群体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
在中等收入群体扩容影响因素方面,宏观层面上,吴青荣(2017)和薛宝贵、何炼成(2018)研究发现高房价、公共服务非均衡、收入差距以及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均会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产生动态影响。微观层面上,李海舰、杜爽(2021)认为当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低,可能是阻碍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因;李逸飞、王盈斐(2022)通过测算中等收入群体或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发现,该群体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普遍较低;基于该特点,许永兵(2022)认为提高居民的投资意识和理财水平,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重要路径。何文炯、王中汉(2022)认为非稳定就业的低收入人群是最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因为其当前所面临的高失业风险、低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短期内限制了其向上流动,提高其就业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影响方面,刘魏(202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打破传统“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方式,突破社会网络的地域限制,扩大社会交往半径,促进居民社会资本积累,进而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张勋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改善了被传统金融排斥人群的金融服务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融资约束的缓解改善了居民创业环境与创业行为,促进了家庭收入增长,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对农村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更强(张勋等,2019);吴雨等(2021)和张红伟、何冠霖(2022)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便利性和金融可得性等途径促进家庭金融理财参与、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和收入水平;张勋等(2021)和唐红涛、谢婷(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居民农业生产向非农就业转型,提高其收入和消费水平;郭晴等(2022)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居民就业概率,还增加了劳动者的单位小时工资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对农村居民更强烈;孙文婷、刘志彪(2022)基于长江经济带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还能通过促进城镇化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秦芳等(2022)从电子商务的角度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增加创业机会等途径提升居民创业水平、增加非农就业以及提高土地流转的概率促进农户增收。
已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群体测度以及群体特征的分析上,相关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进而促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它又通过怎样的途径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流动产生影响?以上问题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家庭收入来源主要可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相对中高收入阶层而言,低收入阶层具有人力资本低、就业质量差、财产性收入低、收入来源少等特点(杨宜勇、池振合,2021)。从低收入阶层的特点与收入结构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能通过如下途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促进其阶层向上流动: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理财参与,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第三,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就业,增加其工资性收入。具体分析如下:
(一)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创业
创业是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家庭成员是否选择创业受到其自身资本水平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信息的获取与金融服务的获得会对家庭创业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张博等,2015;张龙耀、张海宁,2013)。在传统的经济社会中,居民信息获取途径较少,主要依赖社会关系网络,这导致其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较弱。此外,传统金融市场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由于相关金融知识缺乏以及可抵押资产不足等原因,普通居民经常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之外(刘宇娜、张秀娥,2013)。过高的信息成本和融资约束等问题制约着家庭创业决策与收入增长(隋艳颖等,2010)。随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信息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居民获得商品信息与市场信息的成本,帮助其快速了解市场需求(Goldfarb and Tucker.,2019)。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拓宽居民的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有效地解决了居民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缓解了其创业决策中的借贷约束(杨伟明等,2020)。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新的创业机会,例如农村电商和菜鸟驿站等,并且这些新的创业形式相较于传统创业模式具有成本更低、灵活性更高等优点。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信息成本降低、融资约束缓解以及新的创业机会有助于改善居民创业环境,促进低收入阶层家庭参与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进而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二)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理财
居民金融知识储备、金融可得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是影响居民金融理财参与的重要因素(胡振、藏日宏,2017;贾宪军等,2020)。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交易成本高、自身金融知识缺乏和传统金融排斥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其金融理财市场参与率相对较低,阻碍了其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互联网与教育资源的进一步融合,改变了知识供给的内容、结构和形式,使得居民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金融知识的更新(刘魏,2021)。而金融知识的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理财意识和贷款意识(陈宝珍、任金政,2020),打破了知识储备不足对金融市场参与的约束。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缓解了传统的金融排斥,提高了居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缓解其资金不足对金融市场参与的约束。此外,数字经济发展还改变了传统理财中实体网点办理模式,有效降低了居民参与金融理财的交易成本,提高其金融理财参与的便利性(段军山、邵骄阳,2022)。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金融理财市场的参与率,例如截至2020年,普惠性理财基金“余额宝”用户数已经超过6亿,金融市场的参与有助于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三)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就业
传统社会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以及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比例较低的重要原因(武康平、田欣,2020),过高的信息获取成本制约着居民就业匹配。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张艺、皮亚彬,2022),这种新业态的出现促进了就业形式多样化,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例如快递员和外卖员等职业的出现为大量低人力资本、低收入的人群提供了新的就业选择,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数字接入鸿沟逐步缩小、数字覆盖面逐渐扩大。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居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降低了其就业信息搜索的成本,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58 同城”、“BOSS 直聘”等数字化平台的出现提高了居民职业匹配度与寻找工作的便利性,促进了劳动者就业。家庭就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进而促进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H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家庭创业、家庭理财和家庭就业三个机制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微观数据来源于2012 年和2018 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数据库自2010 年开始展开了多轮追踪调查,其调查样本涵盖25 个省/市/自治区,涉及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包括个体特征、经济活动、家庭关系与家庭经济等主题,具有覆盖范围广、数据内容全面和样本量大等优势。此外,该数据库还将家庭收入通过与2010 年相比进行平减,为本研究提供了便利。将家庭关系库、家庭经济库以及个人库中的户主信息进行匹配,最终得到7349个微观家庭样本,其中城乡户籍分别占比47.26%和52.74%,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比42.93%、26.14%和30.93%。宏观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以及同花顺iFind 数据库,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
(二)指标选择
1.被解释变量:阶层向上流动
收入阶层划分主要参考Milanovic and Yitzhaki(2001)提出的将人均日收入介于12-50 美元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的绝对收入划分标准①虽然相对收入阶层划分更能体现公平性,但如果在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相对收入阶层划分的结果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阶层收入过低,甚至会导致无法解决温饱的人群也被划分进中等收入群体。。借鉴刘志国、刘慧哲(2021)研究方法,以1∶6.5 汇率近似计算,以2010 年为基期,将人均年收入介于28470-117650 元之间的家庭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低于下限和高于上限的分别为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通过CFPS数据测算发现,2018年84.55%的中等收入阶层来自2012年的低收入阶层,虽然也存在部分中等收入阶层发生向下流动,但其绝对规模较小,对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影响相对较小①测算结果表明,2018年中等收入家庭共有3520个,其中2976个家庭来自于2012的低收入阶层,占比84.55%,518个来自于原有的中等收入阶层,占比14.72%,26个来自高收入阶层,占比0.74%。,因此本文主要从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视角进行讨论,实证分析仅保留2012年低收入阶层的样本。阶层流动用2012年到2018年收入阶层变动衡量,若该家庭从低收入阶层流动到中等收入阶层或高收入阶层,则阶层向上流动变量取值为1②由于低收入阶层流动到高收入阶层的家庭样本很少,不足样本总量的1%,将其进行合并处理。,收入阶层未发生变化取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
已有文献对数字经济水平的测度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指标选择的思想基本一致。本文参考陈晓峰(2022)的方法,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三方面进行测度,将相关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到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具体指标选择见下表1:
表1 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
3.中介变量
(1)家庭创业。
已有文献常使用家庭是否有人从事个体私营来衡量家庭创业(周广肃,2017)。但考虑到收入阶层流动为动态变量,2012 年或2018 年的创业状态并不能够很好体现创业决策与阶层流动的关系。参考张勋等(2019)的研究方法,使用家庭2012 年到2018 年创业状态的变化来衡量家庭创业。具体方法如下:若该家庭2012年无成员从事个体私营但2018年开办了个体私营或2012年有成员从事个体私营但2018年个体私营项目数增加,家庭创业变量取值为1;若该家庭2012年和2018年个体私营状态以及项目数均未发生变化,家庭创业变量取值为0;若该家庭个体私营从有到无或项目数减少,家庭创业取值为-1。
(2)家庭理财。
借鉴张红伟、何冠霖(2022)的研究方法,使用家庭是否持有国债、股票、基金、金融衍生品或其他金融产品等来衡量该家庭理财情况,持有一种或多种则视为家庭当年参与金融理财。若2012 年家庭未参与理财但2018年参与,则家庭理财变量取值为1;若家庭参与理财状态未发生变化,即2012年和2018 年家庭均未参与或者均参与金融理财,家庭理财变量取值为0;若家庭从参与到非参与则取值为-1。
(3)家庭就业。
王燊成、刘宝臣(2018)使用家庭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家庭就业参与率。但考虑到不同家庭劳动年龄人口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使用当年家庭非农就业在岗人数占非在学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比重来衡量该家庭当年的就业水平。家庭就业变量使用2018年家庭就业水平与2012年家庭就业水平的差值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本文尽可能控制会影响到家庭收入与收入阶层流动的变量。户主层面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面貌①受教育程度使用CFPS标准: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5;大学本科=6;研究生=7。。家庭层面包括: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人口变动、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在业人口变动以及城乡变动,其中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仅计算已完成学业的家庭成员,劳动年龄人口指年龄介于15-59 岁之间的人口。宏观层面包括:产业结构、城镇平均工资、政府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②由于被解释变量为2012 年到2018 年的动态变量,因此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使用2018 年和2012 年差值进行衡量;但由于在相同年份间隔中,各家庭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程度变化差异较小,因此在实证检验中以上两指标使用2018年数据。。
(三)研究设计
在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时,考虑到阶层向上流动为0-1 变量,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假设存在潜变量满足模型(1):
其中, 为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潜变量,π 为常数项,Digeij 为家庭i 所在地区j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γ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Xpij表示反映户主特征的控制变量,αp为第p个户主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反映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βq 为第q 个家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反映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δn 为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独立同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可观测因变量Yij与潜变量
的对应关系如下:
本文仅报告二元Probit模型的边际系数,即低收入群体发生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
(四)不同收入阶层主要特征
表2报告了2012年和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的主要特征。从家庭规模来看,总体上,2018年平均家庭规模相对于2012 年有所下降,低收入阶层家庭规模最大为3.88,收入阶层越高,家庭规模越小;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来看,总体上,2018 年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相较于2012 年有所提高,低收入阶层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介于小学与初中之间,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介于初中与高中之间,而高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超过高中,不同收入阶层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表明受教育程度低也是制约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2018 年家庭人均总收入以及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相较于2012 年均有所增长,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最快;从不同阶层的收入结构来看,低收入阶层收入主要来源为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86.09%,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所降低,分别为76.05%和32.44%,相对低收入阶层而言,中高收入阶层具有更广的收入来源;从家庭创业和理财参与来看,中高收入阶层家庭创业以及理财的参与水平更高,在2018 年高收入阶层中,有超过一半的家庭有个体私营项目,有34%的家庭参与金融理财,而以上两数据在低收入阶层中仅为9%和2%;从家庭就业来看,中高收入阶层家庭就业水平显著高于低收入阶层家庭,2018 年低收入阶层家庭就业水平仅为0.4;从城乡性质来看,2018 年约60%的低收入群体为农村家庭,而超过74%的中等收入群体和超过81%的高收入群体为城镇家庭。
表2 2012年和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群体特征
(五)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性
不同收入阶层并非是稳定静态的,低收入阶层可能因为就业改变、创业成功等原因向上流动进入中高收入阶层,而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因为年龄增长、失业、创业失败等原因向下流动成为低收入阶层。为了体现各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根据家庭的绝对收入阶层和相对收入阶层变动组成收入阶层转换矩阵(见表3)①相对收入阶层划分以“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为标准,将收入最低的25%群体划分为低收入阶层,将收入位于25%-75%的群体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将收入最高的25%群体划分为高收入阶层。。从绝对收入阶层划分来看,2018年我国约有68.67%的家庭处仍在低收入阶层,而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分别占比28.93%和2.4%,表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不容乐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
表3 2012年、2018年收入阶层转换矩阵 单位:(%)
从绝对收入阶层转换矩阵来看,2012 年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到2018 年有72.36%的家庭仍处在低收入阶层,26.67%的家庭向上流动到中等收入阶层,仅有0.97%的家庭流动到高收入阶层;2012 年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到2018 年有65.64%的家庭仍稳定在中等收入阶层,但有25.42%的家庭向下流动进入了低收入阶层,有8.94%的家庭向上流动成为了高收入阶层;在2012 年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家庭中,分别有54.55%和34.09%的家庭向下流动进入了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仅有11.36%的家庭稳定在高收入阶层。从相对收入阶层转换矩阵来看,2012 年的低收入家庭中有41.47%到2018年仍然处于低收入阶层,但有超过58%的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进入了中高收入阶层;超过56%的中等收入家庭到2018 年仍保持在中等收入阶层,也有20.93%的中等收入家庭向上流动成为高收入阶层,但有超过22%的家庭向下流动成为低收入阶层;在高收入家庭中超过50%的家庭仍能够保持在高收入阶层,但也有接近50%的家庭会向下流动成为中低收入阶层。
收入阶层转换矩阵结果表明,我国收入阶层流动存在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缓慢,2012年到2018年仅有27.64%的低收入阶层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第二,高收入群体稳定性不足,2012 年到2018 年有88.64%的高收入阶层发生了向下流动。从收入阶层转换的角度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稳定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提高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其向下流动的风险;二是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帮助其摆脱低收入陷阱,促使其向上流动。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影响的视角,探讨其在中等收入群体扩容和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五、数字经济发展与阶层向上流动实证分析
(一)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基准回归
表4 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在控制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省份特征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272,数字经济水平增长1个单位,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提高0.272 个单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表4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基准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文同。
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和家庭平均年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变小,越容易“停滞不前”;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越容易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教育成为了实现居民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推动力;户主健康水平和党员身份、家庭在业人数增加以及户籍变动均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而家庭总人口和家庭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宏观层面上,地区城镇平均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会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会对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产生负面影响,而地区产业结构无显著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与估计方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改变估计方法,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检验,表5模型(1)报告了OLS 估计结果,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第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各省份单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估计,模型(2)和模型(3)分别报告了以2011 年和2017 年数字经济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三,改变收入阶层划分标准,替换被解释变量。首先,参考国家统计局2018年将年收入介于10万到50万的三口之家划分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对收入阶层进行划分。其次,以相对收入阶层划分重新构建阶层向上流动指标。模型(4)和模型(5)分别报告了统计局标准和相对收入标准阶层划分下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结论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2.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以及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变量会影响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本文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多数文献的做法,选取工具变量并借助IV-Probit模型和IV-2SLS模型对内生性问题进行缓解。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基于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而地形起伏度大的城市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还存在信号不稳定等问题(刘传明、马青山,2020),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地形起伏度属于自然地理变量不会对随机扰动项产生影响,理论上地形起伏度符合本文工具变量的要求。
表6 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缓解的回归结果。第(2)列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后,IV-Probit 模型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AR统计量为46.510,其对应的P 值为0,Wald 统计量为44.910,对应P 值为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第(3)列和第(4)列IV-2SLS 的回归结果中,不可识别检验的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253.161,其对应P 值为0,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的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为210,大于Stock-Yogo 检验10%统计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无弱相关性;Hansen Jstatistic 统计量为0,表明工具变量外生;以上检验结果证明了选择地形起伏度作为本文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以上结果表明,在使用有效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结论仍成立。
表6 内生性问题解决:基于地理工具变量再检验
六、数字经济发展促进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检验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理论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可能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家庭理财以及家庭就业对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进而推动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本部分将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可能存在的三个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机制一:家庭创业
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居民的融资渠道和信息渠道,降低了居民创业的融资成本和信息成本,有助于推动家庭创业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表7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创业机制的检验结果,在第(1)列数字经济对家庭创业的回归结果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创业决策;在第(2)列家庭创业与阶层向上流动的回归结果中,家庭创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收入群体参与创业可以提高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在第(3)列中数字经济与家庭创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家庭创业进而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存在。
表7 作用机制一:数字经济与家庭创业
(二)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机制二:家庭理财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市场(张红伟、何冠霖,2022),这种理财市场参与能否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表8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理财机制的检验结果,第(1)列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低收入群体参与金融理财;第(2)列家庭理财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收入群体参与金融理财有助于促进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3)列数字经济与家庭理财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家庭理财参与,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存在。
表8 作用机制二:数字经济与家庭理财
(三)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机制三:家庭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不仅直接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还能通过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间接创造就业(唐勇、吕太升,2022)。此外,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居民就业信息搜索成本,提高就业匹配效率,进而促进家庭就业。表9报告了数字经济促进家庭就业机制的检验结果①为了避免家庭创业与家庭就业重复,在计算家庭就业时未将参与家庭自营的人员纳入其中。因此,在对家庭就业机制进行检验时,将参与家庭创业的样本进行剔除。,第(1)列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家庭就业水平的提升;第(2)列家庭就业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庭就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3)列数字经济与家庭就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低收入群体家庭就业水平提升,进而促进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存在。
表9 作用机制三:数字经济与家庭就业
七、异质性分析
前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考虑到不同人群在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数字化使用能力以及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部分将讨论该促进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户籍和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群体中的异质性。
(一)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是否存在差异性,以人均GDP 中位数为分类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经济发展水平两组进行异质性检验。表10报告了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低经济发展水平的样本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898;而在第(2)列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样本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为0.265;第(3)列进一步引入数字经济与高经济发展水平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均能促进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但相比之下,这种促进效应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在该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
表10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异质性一: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二)区域异质性
我国不同区域在资源要素禀赋、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历史发展定位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组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表11报告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第(1)列到第(3)列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区域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均有促进效应。进一步,引入数字经济与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区域从东到西,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逐渐加强。可能原因在于:相对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占比更高,传统金融服务可达性更低,居民面临着更强的融资约束,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与低收入家庭非农就业参与的比例也相对较低。随着“数字中国”和“智慧城市”等政策的推进,区域间的“数字鸿沟”逐渐缩小,对于平均收入水平更低、低收入占比更高的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能够发挥更强的作用(马留赟、白钦先,2022)。
表11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异质性二:区域异质性
(三)城乡异质性
表12报告了数字经济对阶层向上流动影响的城乡异质性检验结果,在第(1)列和第(2)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均有促进效应,但在农村家庭样本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均高于城镇家庭样本;在第(3)列数字经济与城镇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更强。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村地区传统金融覆盖广度与深度与城镇存在显著的差异(马述忠、胡增玺,2022),当前中国征信空白的群体主要来自农村,农村居民面临着更强的融资约束,但对于大部分城镇家庭而言,其传统金融服务以及信息的获得水平已经能够满足其进行创业以及理财等活动(张龙耀、张海宁,2013),因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借贷约束缓解以及信息成本降低等效应对农村家庭创业和理财的促进作用更强;另一方面,传统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比例较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钟钰、蓝海涛,2009),数字经济发展为农村低技能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通过促进人口流动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水平,但相对而言,城镇家庭原始非农就业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对其家庭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表12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异质性三:城乡异质性
(四)人力资本异质性
基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进行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分组,将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划为低人力资本家庭,将高中及以上划分为高人力资本家庭①以高中作为划分临界点的原因在于若以初中作为临界点,低人力资本组仅占整体样本量的约1/3,而以大专为临界点,高人力资本组占样本量的约1/3,因此以高中为临界点分组组间样本量差距更小。。表13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人力资本家庭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影响的回归结果,在第(1)和第(2)列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在第(3)列中数字经济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也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高人力资本家庭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红利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的使用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低人力资本的人群其使用智能化与数字化设备的能力较弱,能够享受到的数字红利也相对有限。
表13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异质性四:人力资本异质性
八、结论与启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扩中”和“提低”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的改革,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群体处于低收入阶层。要实现共同富裕,促进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型,就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否会对中等收入群体产生影响以及怎样产生影响是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借助CFPS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缓慢,2012 年到2018 年仅有27.64%的低收入家庭实现了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第三,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家庭创业、家庭理财和家庭就业三个机制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以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加显著,并且相对城镇和低人力资本的家庭而言,数字经济对农村和高人力资本家庭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助力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要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第二,受教育程度低是制约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会影响居民使用数字化的能力以及享受数字经济红利的公平性,要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保证低收入群体及其子代享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公平性,降低教育不足在代际间的传递;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但由于自身人力资本不足的约束,智能化可能会逐渐挤占部分群体的就业机会,导致其收入阶层向下流动,要改善就业环境,稳定并扩大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完善居民就业保障制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陈宝珍、任金政,2020,“数字金融与农户:普惠效果和影响机制”,《财贸研究》,第6期,第37-47页。
陈晓峰,2022,“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考察”,《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28-140页。
段军山、邵骄阳,202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了吗”,《南方经济》,第4期,第32-49页。
郭晴、孟世超、毛宇飞,202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61-75+152页。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2012,“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经济学动态》,第5 期,第12-17页。
何文炯、王中汉,2022,“非稳定就业者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吗?——基于CFPS 数据的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52-64页。
胡振、臧日宏,2017,“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规划影响研究——中国城镇家庭的微观证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第72-83页。
贾宪军,2020,“金融知识如何影响家庭参与理财市场?——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经纬》,第4期,第159-167页。
李海舰、杜爽,2021,“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改革》,第12期,第1-15页。
李强、徐玲,2017,“怎样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北京社会科学》,第7期,第4-10页。
李逸飞、王盈斐,2022,“迈向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结构研究”,《金融经济学研究》,第1期,第88-100页。
刘传明、马青山,2020,“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第75-88页。
刘魏,2021,“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65-77页。
刘宇娜、张秀娥,2013,“金融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经济问题探索》,第12期,第115-119页。
刘志国、刘慧哲,2021,“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经济学家》,第11期,第100-109页。
马留赟、白钦先,2022,“数字经济如何缓解相对贫困”,《财经科学》,第7期,第92-105页。
马述忠、胡增玺,2022,“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劳动力流动?——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303-322页。
秦芳、王剑程、胥芹,2022,“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农户增收?——来自农村电商发展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2期,第591-612页。
隋艳颖、马晓河、夏晓平,2010,“金融排斥对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广东金融学院学报》,第3期,第83-92页。
孙文婷、刘志彪,2022,“数字经济、城镇化和农民增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检验”,《经济问题探索》,第3期,第1-14页。
唐红涛、谢婷,2022,“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70-81页。
唐勇、吕太升,2022,“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城市问题》,第3期,第66-75页。
王燊成、刘宝臣,2018,“就业促进政策能提高城镇困难家庭的就业参与吗?”,《学习与实践》,第12期,第91-102页。
吴青荣,2017,“产业结构变迁、人力资本、R&D 强度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的动态测度——基于协整和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经济问题探索》,第9期,第25-29页。
吴雨、李晓、李洁、周利,2021,“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管理世界》,第7期,第92-104页。
武康平、田欣,2020,“信息不对称与供求失衡下的‘用工荒’”,《经济学报》,第2期,第194-230页。
许永兵,202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3期,第34-41页。
薛宝贵、何炼成,2018,“阶层流动视角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之路”,《贵州社会科学》,第8期,第114-120页。
杨伟明、粟麟、王明伟,2020,“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基于经济增长与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83-94页。
杨宜勇、池振合,2021,“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第30-37页。
张博、胡金焱、范辰辰,2015,“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家庭创业收入——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第2期,第52-67页。
张红伟、何冠霖,2022,“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第2期,第136-143页。
张龙耀、张海宁,2013,“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中国的城乡差异”,《金融研究》,第9期,第123-135页。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2019,“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第8期,第71-86页。
张勋、万广华、吴海涛,2021,“缩小数字鸿沟: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第35-51页。
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2020,“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第11期,第48-62页。
张艺、皮亚彬,2022,“数字技术、城市规模与零工工资——基于网络招聘大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第5期,第83-99页。
钟钰、蓝海涛,2009,“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变动及剩余状况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第41-48页。
周广肃,2017,“最低工资制度影响了家庭创业行为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经济科学》,第3期,第73-87页。
Goldfarb,A.and Tucker,C.,2019,“Digi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57(1):3-43.
Grabka,RBMM,Guebel,J.,Grabka,IWMM,Schröder,C and Schupp,J.,2016,“Shrinking Share of Middle-Income Group in Germany and the US”,DIW Economic Bulletin,18:199-210.
Milanovic,B.Yitzhaki,S.,2001,“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ressman,S.,2010,“The Middle Clas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e Mid-2000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44(1):243-262.
*田艳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E-mail:yptian2002@126.com,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182 号,邮编:430073;向雪风(通讯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E-mail:1655836308@qq.com,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182号,邮编:430073。
【免责声明】《现代财经》微信公众平台所转载的专题文章,仅作佳作推介和学术研究之用,未有任何商业目的;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有侵权或非授权发布之嫌,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2744期)
编辑整理: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陈晨、张晓丹、白晓萌、李茸茸、梁晓娟、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